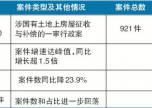之前拆迁的消息一次次传来,但新机场工地的墙最终出现在了东侧1500米外。这里的村民即将目睹周边一座国际化的机场拔地而起,而他们也已经准备好离开这生活了祖辈的故土,因为在远景规划中,这里也是新航城的一部分。

新机场的未来效果图。
记忆中的北京人
北京地方志记载,张家务这一村落形成与元代,当时名叫“张寨务”。而1950年出生的村民周德利说,村里代代流传,明代朱棣定都北京后,先祖们是从山西迁到这里落户的。
——当时这里还没有农田,而是一大片森林,村民们伐树烧炭,卖到北京城里,这曾经是村子里的支柱产业。

村南边的土地上。几百年前这里竟是片树林。
但周德利出生的时候,森林早已消失,张家务已是普通的农村。解放初年生活条件有限,村里百户上下的居民,住的多为土坯房,少有青砖灰瓦的房屋。
还没上小学的周德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买点灯用的煤油。7里地之外的榆垡镇上有供销社,但由于供应不足,更多时候他会步行前往15里地外的安次镇购买。往返30里需要四五个小时,

周德利大叔家里,还养着几只羊。
“自行车?全村也只有一两辆自行车。那时候饭还吃不饱呢。”杂豆面、榆皮面、白薯面等杂粮是当时村里的主要粮食。
至24岁,周德利与北京城里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连续两年,数十位下乡的丰台知青来到了张家务,周德利作为生产小队长负责知青的管理。
“那知青跟村里人不一样,穿戴比农村强多了。即便条件不好,也能看出人家穿得新一点儿、好一点儿,我们农村人还在穿着一代代往下传的旧衣服呢。”

张家务村南侧的菜地。
但他也并不羡慕知青,“虽然是居民,有的家庭生活还不如农民。万一家里兄弟姐妹多,但只有一个人上班,就可能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咱农村嘛,只要肯踏实种地就一定有饭吃。”最终两个知青选择落户在张家务而没有回城。

村里老屋,墙上留着文革标语。
那一两年,往返于市内与张家务之间最多的并不是知青们,而是1955年出生的周德海。
“我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从东西长安街走过。村里有些副业,跟城里有业务关系,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往食品厂、工厂送货。”
那年头街上车很少,从村子到宣武门外校场口的硅整流厂,拖拉机一个半小时就能开到。

张家务村口,如今已经有了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
此时的周德海已经对北京城里人有了一些印象。他开拖拉机之前曾经在成都军区当了两年兵,“有不少西城区的兵来到我们部队。他们没受过累,爬山、挑挑儿都干不过我们农村兵。而且人家言谈举止带着一点儿娇气,也带着一点儿洋气,说话的味儿都不一样,所谓‘北京大爷’嘛。人家背地里不服你连长排长。讲马克思主义?北京兵见多识广,你当官的讲得过人家吗?新兵入伍前,我们常开玩笑说‘又来了一帮老爷兵’。”
改革开放后生活明显好了
周德利的大女儿生于1971年,母亲奶水不够,就只能吃面糊糊。相比之下,1979年出生的儿子命运好得多。
村民的生活因为北京食品厂发生了改变。从1980年开始,食品厂的工作人员来到村子里,商量推广种植小西红柿,用于加工罐装西红柿酱。“比圣女果大,比正经西红柿小,产量还不错,关键是皮厚,好运输、好储存。”周德利回忆到。
北京食品厂与村子合作了约有四五年的光景,每年每户农民因此增加了近千元的收入。“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一承包到户,家家户户不仅吃饱了饭,其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也跟上了。”儿子的营养和穿戴,都比之前强了不少。
周德利家也不再种植自己消费的旱烟,“那块地方也腾出来种西红柿,挣的钱足够买烟抽啦。”至今他仍然习惯卷旱烟抽。

周德利家的小狗,大白菜。
除了西红柿,村子里的沙地多,也适合种植西瓜;怎奈距离市区太院,西瓜的风头当仁不让被庞各庄等著名产地抢走。周德利想,如果能把西瓜运进城摆摊卖掉,又会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于是他借来自行车,把百十来斤西瓜放进两个亲手编织的大筐里,在夏天的凌晨踏上进城路。

村民的家门口。
“卖不了几十块钱,但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不错啦。”他拿着几十块钱来到北新桥信托商店,在那里买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右安门外西二条口或是二龙路的自由市场里,便多了一位卖瓜人。
若是西瓜量大,他便套个马车,在果品公司驻黄村的收购点作价后,直接送到城里的副食店。
1983年我就坐过飞机
1987年,周德利从榆垡镇的供销社搬回来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并不算早,因为周德海1983年就买了14寸电视机。
那时周德海在榆垡镇上的一家织布、制鞋的工厂做业务主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从拖拉机变成小卡车,因为工厂经常能接到来自中国进出口公司的订单,效益挺不错。

周德海大叔,抱着小猫站在家门口。
1983年对于周德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买了电视机、生了儿子,还坐上了飞机。“去广州参加了广交会。镇上工厂哪有这个条件,都是进出口公司给安排好的,咱跟着人家上飞机就是了。这飞机真快,火车都得跑三四天的路程,飞机一会儿就到了。东北、山西我都跑过,后来跟着坐过好几次飞机呢。”
但我最远只去过绥中
下午1点多,周宏义和妻子打开了院子的大铁门,接着100多只羊拥挤着跑出院子,身材高大的周宏义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羊鞭,到几百米外已经收割的菜地里放羊。

周宏义,走在放羊的路上。
90年代初周德海全国上下跑业务那些年,种地的周德利家里也逐步添置了洗衣机、电冰箱、冰柜。而周宏义则选择了进城打工。他来到了首钢,在工厂里做了一名建筑工人。在那里工作的5年里,参与建设了不少企业内的工业与生活设施。

放羊中的周宏义和妻子。
羊肉利润可观,村里养羊的人多起来。五六年前周宏义也开始养羊,一天两次放羊,“养到六七十斤就能卖掉了。可是这几年价钱不高,每年的毛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上下。”
深秋羊还能吃些树叶小草,到了冬天就得喂玉米,“家里种的玉米都给它们当成饲料了。”
这么多羊无时无刻能离开人的照顾,两个十多平米的羊圈不仅拴住了羊,也拴住了周宏义夫妻俩。“农村人,没想过旅游。我最远也只去过绥中,是在首钢工作的时候去那里疗养。”
转成居民户更好
周宏义在铁道边放羊的时候,几百米外村南侧的田地里,白薯装满了一辆小卡车。之前白薯已经收获,品相好的被卖掉,只剩下这些歪瓜裂枣留在田间地头。河南的车主说,将会把这些白薯卖到食品加工厂等地。
“这一车白薯,七八千斤,才300块钱。几分钱一斤。”一位村民老汉带着家人在这里帮助装车,“种地的收入太少了,我们盼着赶紧征地拆迁,把我们都转成居民户。”

这一车白薯,300块钱。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过去那么艰苦,但眼前的无奈,也是我们在城市中无法想象的。
周德利家的土地则是由大女儿来打理。儿子在附近的小学当教师,和他住在一起,照顾爹妈吃喝。周德利有糖尿病,老伴心脏不好,每个月的农村养老金加起来不到千元,“够吃饭?呵呵,够吃药了。”
他也盼着征地拆迁,转为居民户,“大概会安置到榆垡,那里已经在建设安置小区,全都转成居民户。养老金能多一些,吃药看病报销也能高一些。”

村子里的喜庆。
他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最远只去过秦皇岛,是前些年坐大面包车去的。“现在农村什么都有,榆垡就有物美超市。”他觉得自己老了,懒得动窝儿,上一次去北京城里,还是几年前村里组织到展览馆看反腐倡廉展。
周宏义也盼着结束自己的放羊生活,“我才50岁,还琢磨着干点儿别的。”但也没有坐飞机旅游这种“享受”的计划。
周德海家门口堆着晒干的玉米,一只小猫穿梭在里面,“指着它抓老鼠呢。”前些年工厂改革,他退了下来。
新世纪初,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虽然村子里出过不少大学生,但他还是按照老规矩在榆垡的饭馆里,请几家走得近的街坊亲戚喝了场酒。如今儿子落户天通苑,老伴帮助伺候孙子去了。
周德海虽然还留在村子里,“只是为了看着房子。”

周德海家的院子。
故土难离的礼贤镇西里河村
70年代末的一个节假日,西里河村读初中的学生杜建国,为看场电影,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从村里来到大兴电影院。
散场的时间距离下一趟回村的公交车开到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他到电影院旁的自行车出租站,租了一辆自行车往家骑。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虽然到家了,但为了还车,他只好又叫上了村里的小伙伴,俩人骑着两辆自行车返回大兴县城,还车之后,小伙伴骑车带着他再次踏上回村之路。折腾来折腾去,为看场电影,这一下午时间就过去了。

现在的西里河村,村民家的一个局部。
如今,50岁的杜建国开着自己的电动出租车,每天沿高速公路往返于市内和村子。“生活变化太大啦。我们那个年代吃过的苦,现在讲给孩子听,他们都不信啦。”
从马车到每天30多班公交车
新机场航站楼正北约1500米处,便是西里河村与祁各庄村。天堂河从村南侧流过,新机场工程开始后,由于这条河横穿工地,被向北改道,并改名永兴河。河南侧曾有一部分祁各庄村的土地,已被征收。

新机场的未来效果图。
祁各庄村的村委会委员毕瑞良今年58岁,他不记得第一次进北京城的具体日子,只记得“当时我至少是20岁左右了,坐牲口拉车进城太远、太麻烦。”
至70年代中后期,公交车终于通到了祁各庄北边两公里外的紫各庄村,当时一天只有三班公交车。一些村民赶马车去北京城里卖菜,也不得不时常搭上一两个进城买东西、办事儿的人。
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几户村民便分到一头拉车的牲口。然而短短几年过去,随着收入增加,开始有村民购买手扶拖拉机。“我家是88年买的嘛。”毕瑞良说。既要吃粮食又要常伺候的牲口,逐渐从村子里面消失了。
此时大多数村民此时仍在村子里过农耕生活,“因为坐车去趟县城得两个小时。”
几天前下午的祁各庄村委会大门外,一位“兴23”路的公交车司机正在擦洗车身。“我们这车早7点到晚8点,每天30多班,途经附近的村子、礼贤镇,通到大兴县城。”司机师傅说,“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人在县城上班。如果想进城,到了大兴换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啦。”

大兴区属公交车,车站就在村委会门口。
此时西里河村的杜建国在和街坊下棋,自己家里的电动出租车正在充电。不一会儿充电完毕,他沿着京开高速一路80迈,40分钟就开到了马家楼桥。
“我的名字还是到村里插队的知青帮忙取的,当年我正要上学。”杜建国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除了开头那一幕看电影骑自行车的经历,“还有村里街坊骑车去城里卖菜,28加重自行车,后面放两根横杠,挂着两个大筐。”
三四十年过去,除了出租车,杜建国家里还有一辆小轿车。“2011年我买车的时候,村子里汽车不多。但最近几年,眼看着家家户户门口都停上了小轿车,有的人家甚至买了两辆车。”
供销社有猫粮没点心
西里河村最早的一家供销社商店,现在仍然开业。这家供销社有六七十平方米,木头镶玻璃的旧柜台中零零散散摆着各种生活品。灯泡茶叶、烟酒食品、瓜子花生、针头线脑、烟囱瓶胆,连办丧事的黄表纸都有货。

小店里。
53岁的孙凤芬是这里唯一的售货员。1984年她在礼贤镇的供销社参加工作,“我这一辈子卖过的东西可多啦。”然而现在,她感叹网购快递发展太快,让老商店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孙凤芬,还戴着套袖,颇有老售货员的风范。
“刚参加工作不久,供销社里开始有了电视机。听说城里抢购,但在我们这儿卖不出去。”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至1985年后,供销社几乎每天都能卖出一两台黑白电视机。“菊花牌的400多块钱一台,村民们赶着大车把电视机拉走。”
又过了一两年,彩电也开始在农村普及。“农村生活好了,结婚都时兴买彩电。可当时货源紧张,我们一次进货八九台,很快就能卖完。有的人为了抢购还会吵架。”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供销社推出了“储蓄买电视”的服务,即村民可定期将钱存入供销社,供销社按照银行利率计息,至足够一台电视机价钱且到货的时候,通知村民取货。

大门的把手。
1996年,她从镇上调到了供销社西里河村分销店做售货员。逢年过节,五个售货员总要为打包糕点忙碌。“走亲访友,都得拎上一盒。大年初二这一天店里流水能达到2000块钱。”
这样的数字如今小店已经很难达到,“何况当年2000块钱能买的东西,比现在多多啦。”

小店功能非常齐备。
2000年前后小店转制,孙凤芬承包下了这家店铺并以丈夫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冠朝商店”。几年过去,这里只保留了符合部分老人习惯的槽子糕一种糕点,因为“吃点心”已经不再象征着生活的富足。
没了点心却有了猫粮,农村的小宠物也不再是粗茶淡饭、刨垃圾堆。

不服吗?带着猫粮找我来啊。
孙凤芬一直想办法紧跟“形势”,既保留便民店货品齐全的特色,也在进货时更多选择流行的新产品。怎奈生意还是一直下降,“周边小店、超市开多了,大家不再只依靠这一家店。都有了汽车,想买东西去趟镇上或是黄村的大超市也都方便。”

如今小店里还在使用盘秤,卖些瓜子、花生、茶叶之类的。
小店转制、改名已有十多年,快递的电动三轮每天好几趟从店门口经过。但很多村民仍然习惯性地将这里称作“供销社”。
希望野生动物们能有个好归宿
“瞧,野山鸡。”一瞬间,一只长尾巴的野山鸡从公路上飞到了庄稼地里。农村的“野趣”,也是晒暖村民们之间的话题。
据村民们说,庄稼地中的蛇、刺猬、野兔都不算罕见,“黄鼬叼小鸡子,你们城里人称作‘黄鼠狼偷鸡’,现在时不常还能看到呢。狸狗子就是狸子,也经常能看到。”

咱运气不好,没看见什么野生动物。倒是处处可见小猫。
几位村民为一种动物的名称争竞起来,“鼢虫,经常在庄稼地旁边打洞,地面上能看见一个个小土包。”
“城里的记者哪知道鼢虫是个啥。那学名叫地羊。”
描述半天,大家想不出来这种动物到底叫什么,好在有个老乡知道,“你去查查,应该叫鼢鼠子。”
记者拿出手机搜索,原来这东西学名叫中华鼢鼠,是一种挺胖、比猫稍小、尾巴很短的类似鼹鼠的动物。
“我听老人们说过,如果能抓住,用泥巴包起来塞进灶台烤熟,挺好吃的呢。可惜咱年轻的都没吃过啦。”一旁的老村民补充到。

一大群麻雀飞过村旁的田地。
此外常见的便是野山鸡。村民们说,早间年村里并没有野山鸡,至后来榆垡有了野生动物园之后几年,野山鸡变得常见,“可能这家伙是从野生动物园跑出来之后,自然繁殖了。”
原本农民最关心的动物无过于牲口,可这里的牲口耕种模式早已被淘汰。如今的村民们更关注未来的规划,“新机场附近应该会有大片的绿化带、森林,希望这些小动物们还能继续在这里繁衍生息。”
古老的曲艺难以继承
据资料记载,大兴、涿州、固安交界处,于明朝出现过一种曲艺形式叫做“诗赋弦”,如今这种曲艺已经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租车司机杜建国的母亲,便是诗赋弦的民间老艺人。
西里河村“诗弦巷”。不知道是不是和邻村东庄营的“诗赋弦”有关。这些乡村曲艺,谈不上固定的“归属”,十里八乡都流行。
“她70多岁了,村里和母亲同辈、一起唱曲的只剩下一个老大爷。没办法,虽然偶尔还去文化馆演出,但吸引不了年轻人。”杜建国介绍,早年间村里曾有大戏台,逢年过节十里八乡都会来到西里河村听曲,但近些年已经很少有演出,大戏台也拆掉了,一些老爱好者只是在春节才聚在一起唱唱。
“岁数都大了,扮才子佳人化了妆,还是不好看。”
诗赋弦使用与京剧类似的乐器进行伴奏,“曾经有城里的胡琴大师来探访,但毕竟是乡村文化,正应了那两个字:没谱儿。大师只能照猫画虎地学着拉了几段,没有咱村里老弦师拉出来的有味儿。”
缺乏了年轻人的继承,农村也即将变为航城,诗赋弦还能延续多久?“我们从小听这曲艺,挺喜欢的,希望还有乡村能把它继承下来。”
故土难离的村子
西里河村冠朝商店门口的魏石路,每隔几分钟便有一辆满载水泥、渣土的大货车轰隆隆地经过。这些车往返于新机场、渣土场、水泥厂。
一辆大卡车刚刚开过,村民们的三轮车一字排开让路、小心地通过。
“这么大岁数了,除了看着店,也不会干别的,只能盼着多给点儿补偿,咱也能住上楼房。”提起搬迁,孙凤芬苦笑着,“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孙凤芬大姐还是很留恋她的供销社。
杜建国的母亲找不到更多的诗赋弦同好,而今她更喜欢带着老年证免费乘坐公交,定期到香山、颐和园转悠转悠。但杜建国自己却不愿意离开农村,“城里人都愿意去农村旅游,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比城市更舒服嘛。”

西里河村一个小院门脸。
连接着祁各庄村和西里河村的西李路,没有大车经过,格外安静。一辆满载大白菜的三轮车驶来,骑车老汉的播放器里响起经典歌曲《军港之夜》,才稍稍打破乡村的宁静。
静悄悄,静悄悄。
走在这里,不时会有过路村民主动打招呼,“小伙子,去哪啊?拉你一段吧,不要钱。”
毕瑞良说,拆迁已经近在眼前,村里时刻准备着迎接征地工作人员的到来。“很高兴能看见这老农村变成了新机场。但说真的,不愿意走,毕竟故土难离。”
来源:公众号 猫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