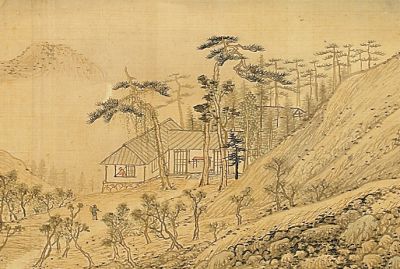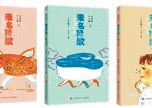从杂志早期广告依旧能看出:女性的很多形象都是弱小的和被讽刺的。与男性想象中强健的“国民之母”相去甚远。
作者:王鑫

《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的封面

从杂志早期广告依旧能看出:女性的很多形象都是弱小的和被讽刺的。与男性想象中强健的“国民之母”相去甚远。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世界文化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启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就包括,1915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妇女杂志》。人们可能对此并不熟悉,但是却熟记另外一本杂志——《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后改名为《新青年》。
商务印书馆参与到中国现代女性启蒙的事业中,除了出版很多和女子有关的读物,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妇女杂志》。当我们穿越百年的历史,重新走近《妇女杂志》,它就像一个生动鲜活的“历史现场”,回响着当时女性启蒙的声音,保守的、激进的、平和的;摇曳着不同的女性身姿,新贤妻良母、新女性、“准摩登女性”。每一次阅读,都是和她们的一次对话,她们真诚的讲述着自己的选择、坚持和改变;她们的期望、努力、困惑、茫然和无助。她们的耳边始终充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要做懂得现代科学新知的新贤妻良母;你们要做妇女解放思潮下的新女性;你们要用拥抱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摩登女性”。每一次走进,都仿佛和她们一起,在日常生活的波澜不惊中缓慢的变化,也经历着历史变革时期的波谲云诡。
虽然这本《妇女杂志》现在少人问津,其中的风景也是“自美其美”,但是其中价值却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被人忘记。透过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我们会知道,被人们今天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观念,曾经有多少人在疾呼,有多少女性以生命为代价践行。《妇女杂志》用事实告诉我们,曾经的女性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争取了什么,才让今天的女性有了这般的模样。
【《妇女杂志》之创办缘起】
应时事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
《妇女杂志》历经17年的时间,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一本女性期刊。在近现代中国,其他女性刊物难以与其比肩,被当时的读者赞为女性报刊中的“第一把椅子”。
商务印书馆为什么要创办《妇女杂志》?虽然很难还原当时是怎样的场景,商务人在酝酿创办杂志时进行了怎样的沟通,做了哪些准备,但是从后来张元济的一首诗当中,可以看出这是出版家的夙愿,“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认为,教育是富强的根本,中国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民智不开,任何改革都没有希望。这其中也包括女子的教育,《妇女杂志》的创办,符合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彼时,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1904年)已负盛名,《教育杂志》(1909年)、《小说月报》(1910年)、《学生杂志》(1914年),也颇有影响。在商务印书馆的市场细分之下,创办《妇女杂志》也就顺理成章了。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个实力雄厚的母体,《妇女杂志》笼络了当时一批著名的文化精英和社会名流参与杂志的创办和撰稿的工作,比如钱基博、吕碧城、向警予、邵飘萍、成舍我、鲁迅、胡适、周建人、周作人、沈雁冰、恽代英、陈东原、叶圣陶、李健吾、丰子恺、叶浅予、陶希圣、庐隐、陈望道、陈伯吹、金仲华等。正因为此,《妇女杂志》的思想价值和启蒙意义都是巨大的。
《妇女杂志》甫一创刊,就得到女学界的极大呼应,并被寄予厚望。当时平湖淑英女校教习张芳芸为《妇女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为:
上海商务印书馆,营书业有年,所出各种杂志,宗旨正大。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事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其于杂志界为藏智之库,馈贫之粮,所谓沈沈黑幕中放一线曙光者……
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民众的心里“宗旨正大”,因此《妇女杂志》被寄望成为女学和女界的“徇路之铎”、“藏智之库”。也有女校校长希望《妇女杂志》能够“通四方之声气”,为女子提供更多的“新知”,更好的实现女子教育。就这样,《妇女杂志》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前景”,呈现了其在中国现代女性启蒙中的模样。
【1915-1920期间的《妇女杂志》】
“新贤妻良母”的塑造
《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共经历六位主编,分别是王蕴章、胡彬夏、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杨润余。虽然六位主编,但是形成的是三个主要时期,即王蕴章时期(1915-1920)、章锡琛时期(1921-1925)和杜就田时期(1925-1930)。
王蕴章是光绪年间中副榜举人,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担任国文教授,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清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15年1月,《妇女杂志》创刊,出任《妇女杂志》主编。
王蕴章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时期,注重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改良和启蒙:辅助女学、宣传科学新知,同时也在培育贤妻良母。只不过,这个贤妻良母是具有“新质”的,具备了新知识、新才能、新身体观、新的“生利”能力。比如,《妇女杂志》的“学艺”、“家政”、“趣味之科学”、“常识谈话”等栏目介绍了大量实用有趣的新知识。当读到现在仍非常流行的蒙特梭利教育方法时,不禁让人吃惊。《蒙特梭利教学法》一书就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没想到能在同时代的《妇女杂志》中被大量的介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强大的翻译实力,使《妇女杂志》中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值得注意的还有,《妇女杂志》刊登不少文章介绍身体的知识,比如身体、性、生育、节育、少女青春卫生等。在1910年代,这些被视为隐私只能通过隐晦和私人传承的内容,在杂志中公开介绍,对女性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身体的解放引发思想的解放。这些“新知”在杂志上公开宣扬,不啻于一声惊雷,让女性猛醒。
王蕴章虽然是旧式文人,但是他熟悉英文,对国外新鲜事物很感兴趣,也经常翻译文章。因此,《妇女杂志》中大量刊载西方女性的图片,并介绍她们的社会生活,“西方美人”成了中国女性的重要参照。“西方美人”的优秀、知性以及报国和兴业之举,被中国男人羡慕,也试图召唤中国女性据此塑造自己。可见,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理想的女性形象是“新贤妻良母”,只不过这个“贤妻良母”是有着中国传统血统,又有现代西方文明知识的“混血儿”。
不过,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鼓吹“贞节烈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受同时代人的诟病,《妇女杂志》的销量也锐减。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使王蕴章对《妇女杂志》做出了调整和改变,但是在新旧压力下,他的努力使两个阵营都无法认同,最终辞职。虽然王蕴章最后黯然离去,但是其对《妇女杂志》的贡献以及对女性的启蒙依然光芒留存。
【1921-1925期间的《妇女杂志》】
新性道德的讨论,引多方人士争论

“舞女牌香发粉”的广告。从服饰可以看出,男女的生活方式都很现代。虽然这幅图片并不能意指女性已经成为性别结构中的主导,但是“准摩登女性”已经开始颠覆与男性之间的结构关系。
章锡琛接替王蕴章成为《妇女杂志》第二任主编,章锡琛23岁进入商务印书馆,随杜亚泉任《东方杂志》编辑。1921 年,接任《妇女杂志》主编。个人命运通常是和时代命运绑缚在一起的,这在章锡琛身上体现的特别鲜明。他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具有新思想,也锐意改革,担任主编之后,《妇女杂志》的模样也从一个“新贤妻良母”转而成为一个具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新女性”。
如何打造这个“新女性”?章锡琛可能未必有一个宏大的设计,但是在他主编时期推出一系列重磅刊号,引发了道德、家庭、两性之间的多重“革命”,这些都关乎“新女性”的塑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将其视为“超前之声”,就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讲,也不啻于一次新锐的“蛊惑”。特别是“新性道德”讨论,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有些言论至今仍有影响。
什么是“新性道德”?简而言之,就是主张一切以爱为中心、为神圣的内涵,主张缺乏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而成的婚姻虽有手续上的全面也是不道德的,两情相悦而产生的爱情和婚姻才具有合法的意义。这种振聋发聩之声,对传统道德和婚恋都是一次沉重的锤击。
章锡琛将“新性道德”的内容进一步放大,认为:
“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
以及周建人在《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认为的:
“一夫一妻的道德也可以不必严限,同时‘恋爱两人以上’,只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旁人也用不着干涉。”
章、周二人的观点把新性道德推向了一个容易引起误会歧义的境地,构成对现代“一夫一妻制”婚姻秩序的威胁。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在《现代评论》刊文反驳,并认为这是一夫多妻制的护身符,甚至会成为一种“流弊”。其实,章、周两人的“新性道德”之意在于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呼唤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以及对两性人格和尊严的尊重,其内容涉及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两性贞操观等,这些是指向传统的旧道德的诸多弊端的。所以章锡琛很无辜地说,“我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上的主张,也无非说明了性道德应该自由的意思,为什么却因为有了借自由去行罪恶的人,便说了该由自由负责呢?”
章锡琛和周建人自然不能接受,双方一来一往,展开辩论,影响颇大。鲁迅的《莽原》杂志也介入进来,北京的《妇女周报》也对此展开讨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实,当我们回溯民国很多名人甚至普通人的离婚案,就会发现,他们的理由大都出自“新性道德”的有关理论。当下婚恋关系矛盾也比较多,所谓“出轨”或者“第三者”往往宣称“爱情至上”,这倒也和一百年前的论调构成呼应,但是,今人可能很大程度是断章取义了,虽然章、周两人呼吁“新性道德”,强调个体的自由,但是在涉及儿童的时候,就有条件了。
“男女间的性的行为,只要他们的结果不害及社会,我们只能当作私人关系,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社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有产生儿童时,总有过问的必要,其余都应该任其自由。”
一百年前婚恋中的问题,迄今依然还存在。看来,如何充分体现个人的自由又能承担婚姻带来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直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肇始于《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争论,对参与其中讨论的个人影响较大。商务印书馆内部和外部均有不和之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此开始实行“内部审查”,打破了主编负责制,这导致章锡琛辞去《妇女杂志》主编职务,后离开商务印书馆。
章锡琛时期《妇女杂志》对于女性启蒙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新女性”的理想形象,这个新女性是“新性道德”中为恋爱自由果敢献身,抛弃旧式包办婚姻中的女性,是婚姻桎梏中敢于挣脱无爱婚姻的女性,是脱离大家庭的制度能与男性建立新式“小家庭”的女性。这个“新女性”不仅是对女性的想象,也承担着男性在新的世界中确立的“新我”投射,还伴随着“人”的觉醒和自立。虽然章锡琛离开了《妇女杂志》,但是他对杂志的贡献和影响也是深远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价值。
【1925-1930期间的《妇女杂志》】
征文与广告女郎,女性两种面孔的交织

关于“新秋之装束”的广告图,图中女性身体健美,服饰现代,是已经告别“家世界”进入公共空间的交际女性形象。
章锡琛离去,商务印书馆将杜就田从编译所的“博文物理部”调到《妇女杂志》担任主编,该杂志由此进入杜就田时期。这时期的《妇女杂志》鲜被学界关注,一是缺乏清晰的舆论主张,二是杂志以征文为主,内容比较贫乏,这两种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杜就田主编时期《妇女杂志》的价值。但杜就田作为主编的魅力虽不突出,时代已经光鲜生动,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浸濡在都市女性生活之中,《妇女杂志》新的女性形象——准摩登女性,开始登场。
杜就田时期的《妇女杂志》是有两副面孔的。一副是从征文中呈现的“苦闷”的面孔;另一副面孔则是从封面和广告中呈现的“摩登”面孔。前者哀怨凄苦,是征文中大量的女性情感经验的呈现;后者则张扬自信,是在现代都市生活“新感觉经验”中的“准摩登女性”。两者构成一种矛盾,同时存在于《妇女杂志》中,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
杜就田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时期,累计刊发征文近千篇,为我们提供了民国女性丰富的个人经验。这些征文文学意义虽然不高,但是文化意义突出。征文中彰显了过渡时期的女性情感,是以“苦闷”做底子,以“悲”、“伤”、“凄”、“苦”、“怨”为色调的一幅暗淡的情感图卷,而这正好印证了新文化的落潮和社会新伦理讨论的不彻底性。
与此相对的,杜就田时期的封面和广告无意之间将女性的“新感觉经验”呈现出来,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准摩登女性”特质。
广告图片中的女性,身体健美修长,服饰现代时尚,发型新颖大方,脚蹬高跟鞋,俨然是一个摩登女郎。这些新生活的体验使女性呈现出的状貌与征文中的女性图谱有着明显不同,不是悲情和伤情的,而是张扬、时髦、现代的。《妇女杂志》的封面和副页中,也出现了一些王少游手绘的“封面女郎”,这些女郎具有时髦和轻佻的双重味道。不过,这些封面女郎与后来的《玲珑》、《良友》、《生活》杂志中的图片不同,始终是虚拟的。
从王蕴章时期到杜就田时期,女性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摩登,从素朴到时髦的转变。女性的气质也由羞涩、含蓄、温婉、谦恭变得自信、张扬、性感、独立,这种女性社会气质转型的背后是女性社会心理发生的改变,尤其是都市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形象的改变,已经使女性开始对自身有了新的“想象”,女性新的生活感觉正在生成。
杜就田时期《妇女杂志》的这种矛盾性,或许表明女性在生活器物层面上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器物层面对女性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这比悬设一个高不可攀的“想象”更能够促使女性发生转变。对这种矛盾性,主编也未必是刻意呈现。无论主观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杜就田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的确将新文化落潮之后,一个多重复杂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混合着“新知识女性”、“准摩登妻母”、“准摩登女性”、“健美女性”和“暧昧女郎” 多重元素的形象。只不过这个“新女性”在器物和消费意识中已经逐渐偏离了五四启蒙时期对女性的期待和诉求。
杜就田之后,叶圣陶和杨润余先后接任主编,只不过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半左右。
《妇女杂志》的命运与商务印书馆裹挟在一起,1932年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那场文明的悲剧也让《妇女杂志》就此停刊,此后再也没有复刊。尽管如此,《妇女杂志》作为贯穿民国十七年历史的重要女性媒介,清晰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的多重样态,价值不言而喻。《妇女杂志》虽然是面对女性,但是杂志的主编以及主笔,都是以男性为主,中国现代的女性的启蒙,男性始终扮演着“导师”的身份。
我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一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份杂志。在此,是要向商务印书馆表达深深的敬意的,《妇女杂志》就像“徇路之铎”,它让我们知道今天的女性从何而来,如何才有了今天的模样,以及在启蒙之路上,所历之艰辛。于今天的女性来讲,我们惟有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女性之权益,富足思想,成就自身,才能慰藉所有前辈女性平凡和伟大的生命。王鑫
(33版到35版图片选自《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
相关阅读

王鑫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