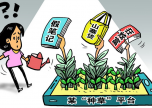2017年6月22日讯,2012年秋,长篇小说《繁花》悄然面世,随即轰动,畅销,一路拿奖,至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一口气“登顶”。如此横空出世——这在顶层深固的文学市场上,几乎是个奇迹。期间,《繁花》影视版权被王家卫买下,时不时冒出选角新闻,一阵嚣腾。
作者:吴越

《回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虚构《碗》插图,牵过浑身白霜的马匹,风雪迷目,我上了马。金宇澄手绘。
上海作协小楼,常有不同人群扛着机器来《上海文学》杂志社拍“金老师”,而他总是在那间他做了24年编辑的旧房间,堆满东倒西歪书的书桌一角,接待电视台、电台、视频网站、报纸、杂志……种种询问与探究。夏天,身后阳台爬山虎绿得烂漫,秋冬,瑟瑟西风从南窗穿过。采访间隙的静时,他会低声重复一句,“到我这个岁数本不该再写作了”。他怀着不能泰然领受的愧色,自比忽然成名是“老妪怀孕”。
几家出版社殷勤介入,使他的旧作一些一些整理出来,人们又才发现,他不仅会写上海的时尚变幻,还会写东北的野地、苞谷、钉马掌,不仅会写一场一场评弹般的饭局,还会写劳动,写饥饿,写惊心动魄的死亡。对金宇澄的认识,缓慢铺开一角,但直到他追迹父辈生命历程的《回望》出现,你才可能在刹那间看清,金宇澄写作的前史与背景、愿望与意义。
像瓮中陈酒,金宇澄的故事是一点一点流泻出来的,而现在比前几年更适宜于品味了。
1

金宇澄 戴显婧摄
1955年7月15日,姚云给丈夫程维德写信:“舒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她很有兴致地记述,写这封信的上一个星期日,抱舒舒去看医生,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舒舒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时问了一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金舒舒最初与马的对视与发问,折叠于陈年信札中,一个甲子之后,小说家金宇澄——也即当初的金舒舒,展读母亲记录自己幼儿时期,感觉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但他仍然记得那匹白马。1950年代,上海淮海路街头,确实有马匹的活动。清晨有人牵着挂铃铛的母马走过,挨家挨户叫卖马奶,有人要买,当场就挤。那时居住上海西区的孩童,有金宇澄,也有王安忆。类似景致,王安忆在《弄堂里的白马》里亦曾提及。上海街头的白马,惊异了多少童眸。
1968年,金宇澄初中毕业,加入1969年“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喧嚣,船载车运,他被投放于东北边境黑河的嫩江农场——在寒冷的原野上,他与马匹真实结缘了,“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臊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菱草那种切碎了的、秋天野花的气味”,他见识到“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温良”,动容于马匹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终身被使役,“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只在偶尔的时刻,它们才显露刚烈的本性。
马匹一样沉默的劳作,半军事化的环境,一切都那么生疏,田间采下的青椒,本地人吃苹果那么拿起来就啃;凉菜“大拉皮”,生拌的卷心菜、胡萝卜丝,一切都与当年的上海习惯不同,难以下咽。反过来,几个上海小青年到田间采一铁桶的青毛豆,马厩里抓一把粗盐煮了就吃,当地老乡同样感觉极其怪异,“你们究竟是人还是牲口?这是破坏革命生产!”
很短时间内,金宇澄在田头吃午饭,已可以随老乡一道,折断树枝当筷子。难得吃一回肉,他和众人同样,下筷如雨,即便夹出一只误入热鑊中屈死的小老鼠,也只是随手弃之于地,继续下筷,吞咽。八年中,他变身为北地的熟练农人、泥瓦匠和马夫,内心的上海生活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他完全理解了对于“上学”、“病退”重回大城市,何以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理想。患胃溃疡以后的一个月中,他曾经冒名为6个上海青年拍摄胃部“钡餐”X片,最后被放射科上海老医生察觉制止这自弃式的“疯狂”。青年的他,热气腾腾,对前路却刻意颓唐。这一切,又要从本文开头,母亲写给父亲这些信文说起。
2

1971年,已在黑龙江嫩江农场务农四年的上海知青金宇澄(左)和哥哥金芒(右)合影。
父亲原名金大鹏,学生时代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1940年来到上海,受中央社会部系统的吴成方领导,化名丁弢,在汪伪背景的《市声》半月刊任编辑,按指示迁入今复兴中路淡水路一处居所,与系统的同道程和生(后牺牲)假扮兄弟,从此化名“程维德”。1942年7月29日深夜,给中共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日共党员中西功被捕,供出多人地址,父亲在寓所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刑讯多日,下肢几乎瘫痪,未泄露系统的任何秘密。1942年10月,他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关入南市车站路汪伪监狱及杭州监狱。1944年底,经组织帮助,以“重病保外治疗”方式出狱,后在汪伪宣传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次年奉调淮南华中情报部,经过多次汇报谈话“被捕出狱经过”,得到审查结论——“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但并无书面结论,为十几年后埋下了隐患。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受赐于这次牢狱之灾。母亲姚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活泼秀美,家里经营银楼,衣食无忧,像那个年代培养浇灌的大量青年,思想进步,渴望救国。抗战胜利后不久,姚云在老师朱维基家,见到了一位大她七八岁的陌生男子程维德,他是1942年朱维
南市监狱的难友,时为《时事新报》新闻记者。朱维基当时办了一份《综合》杂志,发表过姚云所写一篇巴金《憩园》的读后感,而程维德在这本杂志上写过不少才华横溢的社论和散文。共同爱好文学的关系,两人开始交往,程维德常常主动打电话来,借书、还书;姚云也曾随程维德参加国民党市府的记者招待会。两人相恋数年,跨越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等大事,于1950年成婚,彼时,姚云从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短期训练班”结业,夫妻双双在上海总工会工作。
1955年4月,维德调任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5月,全国开展“肃反”运动。那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儿子,后一个女儿,老二因生产时特别顺利,取名“舒舒”。6月7日夜,维德留下一张字条,称有要事去北京出差,没写去哪里,带走了一些替换衣服。起初姚云并不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多天杳无音讯。直到6月28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带来一封没封口的信,是维德报平安,称是去完成“组织任务”,仍然没有回函地址。姚云当晚写了回信,来人第二天来取。如此一来二去一直通信,姚云事无巨细记录家中老人孩子的大事小情、财政支出、工作情形——关于二儿子舒舒的萌言萌语,就这样写进了7月15日的信中。维德有信必复,洋洋洒洒,谈天说地,但是一直回避“为什么一去不回?”“什么时候能见面?”等问题——事实上是他无法作答。他本人早被禁闭在一幢陌生小楼里,反复默写交代材料,很久以后他自己才知道,小楼就在淮海中路,离家只有两站路。
悬心等待四个多月,等到了组织方面找姚云谈话,正式宣布维德是“潘汉年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开除党籍,工资停发,至此,丈夫再没有片纸来函。
经济拮据,孩子们都不再去托儿所,单位分配的住房随之被收回。这个革命家庭早期的完整、静馨与甜美,就此停顿。
3

散文集《洗牌年代》插图,“马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金宇澄绘。
父亲回家是在1956年底。他的结案,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虽查不出与“潘案”更具全的内容,仍然被调至轻工业工会当一般干部。母亲则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每两周回家一次团聚。
1959年,上海市建委在湖州小梅口建水泥厂,父亲被调去筹办,母亲决定也一起去湖州,甚至做好了迁户口的准备。就此父亲做总务工作,上海、湖州两地跑,母亲驻湖州,中文系的学历,却去负责水泥厂化学实验室创建工作。家里常年由保姆照顾着三个孩子和祖母——对于金舒舒而言,儿时最亲厚的人是从黎里老家来沪的这位老者。若干年后,读者在长篇小说《繁花》中,读到蓓蒂和绍兴阿婆纷乱时世的相依为命,想必是这份祖孙情的再现。
1960年,水泥厂转交浙江方面经营,母亲才得以回上海工作,一家人再次团聚。当时金舒舒已经上了小学。他遇到了社交的障碍。“舒舒”两字无论上海话还是普通话读来都不甚好听,且作为一个男孩名字,多少有些怪异。父母忙于自身处境的劳作,见报上号召全社会支持“民办小学”,就为他报了名,根本不知道这种非正式的小学,条件一塌糊涂,教师是初通文墨的上海弄堂妇女,教室也就是弄堂居民家,与解放前张乐平先生画《三毛流浪记》中弄堂小学,楼上人家洗衣漏水,楼下或楼梯台阶坐着打伞上学的小孩殊无差异。因为地点都由弄堂热心志愿者提供,常会变动,这学期在长乐路、新乐路,下个学期可能就在思南路,频频换班。每换一个地点,插一次班,老师就在黑板上书写“金舒舒”三字,在哄堂大笑中,介绍这位新同学。老师经常拎这个小学生的耳朵,金舒舒因此沉默而内向,习惯性逃学,性格孤僻,不喜交友。他总是独自游荡街头,手持一枚大铁钉,每一天在陕西路“凡尔登花园”的围墙上,一路画一长道深痕;在小书摊翻书,去襄阳公园收集植物标本。俟“文革”初期的某一天,少年金舒舒终于提出来,他的名字过于资产阶级化,要改,父亲才似有所悟,引了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句,为他更名“宇澄”。
虽在知识分子家庭,但不曾有谁明确地把他往文学的道路上教引。他少年记忆中,父亲被定格为一个长期独坐伏案的寂寞身影,父子间很少交流。父亲曾做过多种职业,包括记者、编辑、剧本作者,喜欢旧体诗,颇有写作才能,但自儿子记事起,父亲的全部写作就是追迹和申诉。针对不同的问题,每一份都很长。
其实能与父亲共话一室的机会都是稀少的。“文革”前夕,父亲被安排在地处上海郊区吴泾的建工局技校当语文老师,每周在徐家汇搭校车回家一次,还常带一大摞作文本回来逐字逐句修改,留给儿子的时间极其有限。“文革”开始,从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七九年三月被彻底“平反”,父亲扫了十年学校厕所,写了十年“交代材料”。
说起来,母亲出身复旦中文系,同样雅好文学。但她的工作长期是宣教、动员、布置展览,去工厂做深入的女工调查等等,从上海总工会机关转到湖州水泥厂后,更是彻底改行学水泥配方。引发金宇澄对文学兴趣的,是“文革”期间的地下阅读氛围,是八年北方生活接触的1949年前后西方/苏俄小说,是图书馆系统中流出的“毒花毒草”在社会毛细血管的输送。
最初的写作练习,是他在东北时期大量描述东北的生活情况、黑龙江和上海的反差的信。主要的一位上海信友,没有下乡,大他三岁,熟读黑格尔、叔本华,有一次对方在回信中说:你写得太好,以后应该可以写小说。
其时他也给家里密集写信。写所见的东北劳改农场情形。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都不予回应。这种搁置,要等很多年父亲去世后,他翻检父亲1942年的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报告等等内容,才能够正确解读。他才明白,当初他信中强调的那些景象,父亲是完全懂得的,只是父亲“不响”而已。
4

《洗牌年代》 文汇出版社
1978年金宇澄返城,进入一家钟表小企业,这个范围的人们,热衷于钟表的“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他会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对他讲钟、讲表,怕听嘀嘀嗒嗒声音。践如那位信友的预言,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觉得可以写小说,可以投稿。1985年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次年发表《方岛》,获得了两届《萌芽》小说奖——那时《萌芽》还不是一本青春文学的刊物。1987年,《风中鸟》获了《上海文学》短篇奖。1988年,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任编辑。
回到上海后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里,金宇澄一直在追溯东北记忆,历历在目:他写出上海女青年眉宇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引动男青年思念“连绵阴雨的马路、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沪剧女角的唱段”——是在东北洋葱田里劳作时,感受到遥远的上海(《不死鸟传说》);他写冰天雪地的站台(《夜之旅》),写“六百公顷的玉米在视角里难以形容”(《欲望》);他写被评论家以为作者是“北方作家”的村妇故事(《譬喻》),以及棺材匠的苦恼(《风中鸟》);他写到诸多难以忘怀的知青死亡事件——“阿桂”的故事,在经历了三十年世事淘洗后仍不能平息与释怀,于2011年还原、丰实为更长篇幅的非虚构《碗——死亡笔记》,在该年《钟山》杂志发表。)
他渐渐写一点上海,基本是富于画面感和故事性的散文,像是慢慢恢复了对这座城市的话语权。金宇澄1988年的短篇《标本》,似乎暗示着与东北题材的告别。小说中,博物馆晦暗潮湿的大厅深处,几匹白马的肚腹已被掏空,眼眶中装了玻璃假眼,制作员移动马匹的庞大躯体时,马蹄磕碰了精细、陈旧、华贵的栗木地板,“这种缥缈不定的声音,如同梦里的碎步”。
黑河在远去,白马入梦。上海归来,肉生肌丰。
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重“乡土”轻“城市”,金宇澄则发觉城市中也有泥土——丰富的有机质——也就是人脉。城里人都有其出处,你从哪里来,上一代人过得怎么样,如何维生,如何变迁,同样形成丰富、生动的景深,尤其上海这样的移民大城市。金宇澄父氏家族吴江里黎的古镇传奇,与母氏家族从南京、宁波迁至上海南市、开银楼兴衰的经历,在血脉的阡陌中微翕响动。他绘制了不少的上海地图,其中一幅标出父亲母亲于1965年之前居住过的地点,竟有近三十处,包含上海“上只角”、“下只角”,纵贯南北,遍布市、郊。
城市其实同样辽阔、深邃而致密,如田野,如山峦,如溪涧。人们如植物般展开茸须与触角,在疾驰的日脚中扎根或飞翔,留下声音和故事。
5

《繁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父亲眼中,儿辈写作成为小说家,成为文学编辑——某种程度上,应视为自己的同行,但他从不乐观其成,相反几乎是忧心忡忡地侧窥着。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的铅笔字:“……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进入老年,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只这样在信件和读书笔记中写一些感受。这段激扬的、有警示色彩的话,金宇澄认为,是“我爸为我写的”,像是寄语。因为,青年作家金宇澄,似乎表现为父亲年轻时的反面——较为“消沉”。
父子之间,通过如此间接的方式进行交流。
在金宇澄的整个成长时期,父亲几乎都是不在场的,但父亲的“问题”却总是在场。时代之手就是这样极其顽劣地在千万个家庭、几代人的命运里捏造了一些永远的隔阂和障碍。
不久,金宇澄所在中学有插队去东北农场的名额。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军垦、兵团是不能去的,金宇澄毫无选择,平静地报名。
此后双方关系便进入传统的“中国式父子”模式:情深如海,无话可说。父亲一生的跌宕,生前几乎没有完整对家人说过,只有在父母亲偶尔因遇见某人或某事而起的交谈中零星听到一些。出于对文学、历史画面的敏感,常常只说一遍他就能记住,比如日本人监狱里听见日本狱卒唱俄文歌、狱中如何的饥饿状态,汪伪监狱的混乱管理……
20世纪80年代直到离休,父亲似乎平静下来,一直做上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90年代有几年时间里,父亲与一位马姓旧友隔天要通一张“明信片”。当年这位老友搭救他出狱,但两人之间无“横向联系”,碍于纪律无法相谈,而后1949年至“文革”疏于往来,又过几十年,重新联系上,已都入老境,终于可以密谈。反正都是别人看不懂的旧话,双面蝇头小字,工工整整,直接写在明信片上,你来我往,十分热烈。几年之后,老友去世,家人将一厚沓明信片奉还。从此,再无人可话当年了,父亲将明信片锁入抽屉,不再翻阅,更为沉默。
2011年5月的某一天,金宇澄在“弄堂网”上以网名“独上阁楼”写了开场白,最初只想写自己所知的人与事,在跟帖者“追更”声中,无意间写出一段密集的人物对话,胸中无数话语压抑不住地开腔,他忽然意识到,这是长篇小说开始的一种独特的调性……这也就是写透上海世态人情、时代幽明的近40万言《繁花》。
翌年秋,《繁花》在《收获》刊出,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翻看过这两个版本,不知是否读完,不发一言,在该年的6月去世。在这部小说的深处,金宇澄藏匿了父亲离休后与情报系统老上级在静安公园茶室碰面的画面:双方凑得很近,照旧压低声音说话,犹如旧时接头,对方穿来了1949年前压在箱子里的全套西装,举手投足,如出土文物。父亲告诉对方,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代人、包括他们的仪式感,已失去意义——金宇澄至今不知道,父亲是否读到了这些章节。时间被彻底停滞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情绪很差,往事纷繁,同样体现在她不时翻看的旧相册中,话头绵绵无尽,金宇澄请母亲依照片写下时间的说明次序,等于一个人最后对自己的证明。在半年内,母亲做了两大本的剪贴,完成了给自家孩子看的“口述实录”。在整理物件期间,母亲交给他三封父亲给马姓朋友的旧信,拿回来放了有一个礼拜,一天深夜,金宇澄打开父亲的旧信,读到1942年7月被捕前夕的那个晚上,饭后眺望延安中路方向的外国坟山(即今之静安公园),“黑黝黝的,夜光隐隐然照见地些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不知怎么,心里惆怅,很不愉快。十二点多步行回寓所,上床大概一点了,过不多久,突然前面电铃声大作,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
父亲的叙述那么有画面感,燃起火花,使他决意写作。于是就有了《繁花》之后的家族传记《回望》,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列出他据史料文献、友人书信,爬梳、整理、考证补充的父亲故事,母亲的口述实录以及多种日记、照片等内容。这也是他与父辈的一次特别的沟通——将阴阳永隔之间的对话,落在纸上。书封“回望”,是他自己的字,白色竖排,有读者说乍看像是“面壁”——也可这样理解。
完成《回望》,金宇澄认为它饱含了实验的意义,通过“不完整”的书写方式,拼接父亲母亲这对普通男女的发展轨迹:怎么踏入社会,怎么产生选择和承担,连接成一条属于他们的曲折线路。笔意尽处,他无法不感到人生的某种宿命——“我一直认为年轻人的世界很宽广,实际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眼前,世界一直是狭窄的,很多人往往是一天一时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一生。你的背景、你的性格可能早已决定了自身的命运。”
6

中篇小说《轻寒》插图,金宇澄手绘,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7月出版。
2017年1月,《回望》出版。对于作者配合出版社如何为新书宣传,金宇澄一直迟疑,经常想到父亲的低调姿态,写作中激荡的心情,此刻逐渐冷却。
2月,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辗转发来一个微信名片。“看了《回望》,没想到我姑爷爷当年说的话,全部是真的,”一位现居德国的沪籍男士读者来信说,“我小时候住上海,我姑爷爷放出来后,第一次陪他散步,在华山路武康路,他告诉我黄金荣送过他一幢别墅,就在附近,我很吃惊,不可思议。说那时他在淮海大楼住过。包括您书中关于他的记录,我们几乎不相信,永隆大楼住过,锦江住过,华山路住过,居然上海法租界几乎是最好地段他都住过。我一直对他有好奇心,只是当时画画,又准备出国,很多家里的活动没参加,所有人都充耳不闻,认为他在吹牛,没想到都是真的。”信中提到的姑爷爷,就是金宇澄父亲的老上级吴成方。
这个回声,令金宇澄百感交集,也见到这本“家”书的价值。个体的人在每个时代里呈现了一种消耗,若不趁着记忆及时记录下来,留住回眸,便正如后人看到一张只有影像没有说明的旧照片,将永远无法得知它的确切内容。
“上代人已经结束,我这代人也完全老了。承前启后,是这么过来的,写作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把曾经的细节记下来。这是没人做的事,历史学家不这么做。”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