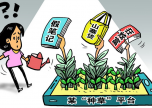重庆7年白修德为何与《时代》决裂 揭秘一个历史记者的诞生
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电影《第一夫人》将在国内公映,这部杰奎琳·肯尼迪的传记片,去年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影片中,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杰奎琳面对记者采访,陈述自己遭受的生死剧变。
作者 沈沣
这位记者在影片中没有具名。他是白修德。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漫长的记者生涯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跌宕起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时代》战地记者报道中国抗战。二是战后出走《时代》,远赴欧洲,报道冷战中的欧洲;三是回到美国,跟踪四届美国总统大选,写作《美国总统的诞生》,颠覆了美国大选报道的常规。由此,肯尼迪遇刺之后,杰奎琳选择采访者,白修德自是当然之选。
当白修德坐在杰奎琳·肯尼迪面前的时候,他发现“第一夫人”最为困扰的,是历史怎样评价她的丈夫。杰奎琳一遍一遍地在白修德面前重复“历史”这个词,“历史,请对约翰·肯尼迪好一点。”由此可见,杰奎琳请来白修德,并非让其写一篇新闻稿,而是来写历史的。
1976年后,白修德完成个人传记《追寻历史》,进一步详述其在中国抗战时的心路历程。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探索历史》的书名出版,去年底由中信出版社再版。
《追寻历史》可以称为“一个记者的诞生”。白修德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是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正是在费正清的影响下,他选择中国作为事业的第一站。
白修德初到中国,资历尚浅,他也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来自异域的观察者,一个坐在打字机旁的收集者。“如果要用历史去包装整篇报道,那么掌握决定权的是远在纽约的主编们。……把历史留给纽约去书写。”白修德因缘巧合被《时代》杂志选中,成为《时代》聘用的第一个特约作者。受到老板亨利·卢斯的影响,不惜掩饰与粉饰,他和《时代》一起把蒋造成“英雄”。出于这样的新闻观念,白修德在很长时间对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充满不实之词,很难说到底是出自白修德之手还是纽约的编辑之手。《纽约客》的专栏作者项美丽在其中国回忆录中,评价白修德的报道“太重表达他想看到的,而不是他实际看到的”。
正是因为大时代的风云际会,让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得以出入于历史巨人之间。新闻同样可以有史家之笔,讲述人的故事。白修德在《美国总统的诞生》中一书中就谈到“政治的核心是领导人物在强大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非凡素质”,就此观点,和亨利·卢斯别无二致。两人亦均热爱中国。不过,历史由人书写,却不由人捏造。当白修德已经在1942年大灾中的河南,看到蒋介石政府的谎言和无能之际,卢斯和他的《时代》仍在徒劳地虚构蒋的未来。
审视历史,可以修正现实。纵观《追寻历史》一书,在时代的大潮裹挟之中,白修德时刻有立场选择的困惑,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通过自己的调查去不断矫正,并且并不满足于对时代做碎片式的记录,而希望能够加以拼接。战后白修德从中国返美,他与《时代》同事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披露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倒行逆施,已视蒋为“历史罪人”,提前预告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此书轰动一时,但不久赶上美国麦卡锡主义抬头,他由此被打上“左翼分子”标签,被亨利·卢斯视为“《时代》的叛徒”。
一般概念而言,新闻是对新近事实的报道,换个时间的角度,新闻也可说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当年白修德选修历史,感叹到“这是我做过的最危险的选择”。
重庆七年,白修德为什么和《时代》决裂?
费正清的第一位学生
白修德是犹太人,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街区。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正赶上美国的大萧条时期。白修德家境贫困,16岁时父亲去世,当他从拉丁语学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有轨电车上卖报纸。由于得到了一份报童基金给予的180美元,再加上哈佛大学提供的奖学金,1934年白修德进入哈佛大学。
白修德大一选修历史,师从名教授罗杰·比奇洛·梅里曼,梅里曼主张“历史就是故事——因此,要讲得有趣”。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的筹划下,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哈佛燕京学社,如今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是亚洲以外地区关于东方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因为人少的缘故,白修德常常跑到那里自修,由此对中文书籍产生兴趣。“它们散发着独特的霉味,不同于西方书籍所散发的霉味。”
于是,白修德决定在大二选修中文和中国历史。“这是我做过的最危险的选择。”靠着死记硬背,到毕业时白修德能够掌握3000个表意的汉字。不过晚年基本都遗忘了。
因缘巧合,白修德成为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学生。当时29岁的费正清刚刚结束在清华大学的执教回到哈佛。因为白修德是唯一主修中国史的本科生,因为费正清成了他的导师。“他说话温柔,拥有能挑动人心的交流天赋,总让人在回味时品出他的幽默。”
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费正清说:“令我最感高兴的学生应该是我的第一位学生,但那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在书中,费正清把白修德的回忆录《追寻历史》评价为“富有勇气而才情焕发的长篇小说”,不过“唯一没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跟他初次见面时的兴奋之情”。
费正清称赞白修德“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头脑,也懂得谋生维艰的社会现实”,但是缺少人情世故。
听从费正清的建议,白修德的毕业论文题目选择了“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以专业最优的成绩毕业。他放弃留校,决定去中国。“费正清知道埃德加·斯诺去了中国,他认为我应该尝试取走斯诺正在走的道路。”
做了一篇假报道
1938年白修德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因为上海是个可以找工作的地方。”期间去了天津和北京。
他把自己定义为“观察者”:“这是一座充斥着怪物与传教士,光与笑,恶棍与花园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黄包车,在城内四处游走,四处观察。在这个城市,底层人民的绝望之深,是会令波士顿穷孩子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而其上层阶级寻欢之堕落,则是会令波士顿精英阶层都觉不可思议。”
但是,在上海白修德找不到让报社感兴趣的新闻,1939年他来到了重庆,受雇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担任顾问。实际工作就是给外国记者提供所谓“新闻”。“一个外国记者,到重庆的当晚就获得了政府的邀请,整整四天都沉溺在杯盏之中,往往是酒还没醒,酒东倒西歪地去赴另一场宴会了,他们的通讯稿都是我在新闻委员会的办公桌上代笔完成的。”
在重庆,白修德发现自己的哈佛学历管用得多。“哈佛毕业生在蒋介石重庆政府高官中占比之重,是他们在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政府高官中都达不到的。当然,现在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一切就是场大悲剧。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这批人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
白修德在此期间还泡制了一则假新闻。他看到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浙江某地一个叫蔡黄花的女人,在日本军人聚集的妓院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杀了不少日本军人并成功脱身。白修德把她包装成了游击队队长“蔡金花”,年纪轻轻,腰上别着两把手枪,并不断地给国外媒体提供佐料。蔡金花的故事传到美国,成为仅次于宋美龄的抗战传奇女性,后来《时代》周刊还打算重新追踪她的故事,白修德不得不站出来反对,承认自己是这则虚假报道的始作俑者。
做了几个月时间的顾问,白修德获得美国《时代》周刊邀请,成为“特约记者”。
实际上,白修德只是为《时代》收集新闻素材,在美国由编辑进行改写。“我要做的就是为新闻提供背景资料,然后‘邮寄’到美国去。杂志社对时效性很强的、突发的中国新闻不敢兴趣,我所写的必须是在6周或两个月内都不会失去新闻性的报道。”
白修德迫切需要采写一篇大新闻,来获得《时代》的认可。1939年9月,他决定去中国北方调查战事。
国民党官方给他开具了一张低级别的军事通行证,虽然得不到当地的优待,反而方便了他自由穿行战区。“如果我拿到的是发放给著名记者和达官显贵的贵宾通行证,那么我往返前线的路上都一定会有人陪同,我就什么都观察不到了——这一点在30年后的越南战场上得到了印证,当时的我已经非常有名了,因此,我被官方牢牢看着,不让我接近真相。”
在山西前线,白修德开始认知战争的残酷。他在报道中写道:“一个接一个村庄被彻底摧毁。房屋被暴力损毁,又纵火焚烧,枪毙都是被熏黑的痕迹,桥梁也毁了。日本士兵烧毁房屋一是为了解闷而肆意胡作非为,二是为了生火取暖,消除寒意。”他的通讯稿占了《时代》杂志一页半的版面。
在这次前线调查中,白修德结识了战斗中的一些共产党人,比如一位姓吴的游击队长,共产党人的战争经验和群众工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山西之行让白修德有了认识的转变:“在返回重庆时,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与他们脱离。”
调查“皖南事变” 《时代》不感兴趣
1941年1月,白修德结束了在东南亚的采访,回到重庆。正值“皖南事变”爆发。
他开始着手调查,在数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大量政府文件、秘密指令以及自己的采访笔记。在重庆,媒体都被国民党政府控制,没有刊印任何消息。“我能觉察到杀戮的回响,但那声音太过模糊。……适合新闻报道的故事消失了,我所能讲述的只有历史。”
在6月,白修德采访了蒋介石,他对白修德说:“日本的侵略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在皖南事变发生两周之后,白修德采访到了周恩来。“我们从那时起便成了朋友。”
白修德问周恩来:“蒋介石当时是不是在对你撒谎?”
“不,”周恩来说,“有人在对总司令撒谎,但总司令的话里也掺杂了谎言。总司令撒谎的目的是想要巩固自己在各派系中的位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利用国内所有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越大。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他将一败涂地。”
白修德将周恩来称为他见过并了解过的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人是史迪威和肯尼迪。
在《追寻历史》之中,他对周恩来赞不绝口。早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时,白修德就认识周恩来了。“他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很喜欢指导我这个菜鸟,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一次,白修德接到了周恩来的宴会邀请。主菜是一道烤乳猪。白修德告诉周恩来,他是犹太人,虽然在离家千里的东方,他已经打破了不少清规戒律,比如喝酒。
“特迪(白修德的昵称),”周恩来拿起筷子,指着乳猪说,“这是在中国。你再看看,看看。在你看来,它像猪。但在中国,它不是猪——它是鸭。”白修德吃了人生第一口猪肉,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坚持不吃猪肉的传统。“周恩来这个人是可以让你相信猪就是鸭的。”
白修德以为《时代》周刊会对皖南事变的报道有兴趣,实际上,《时代》毫无兴趣。他关于此事的报道,最后只刊登了“一两段而已”。
最后一次被蒋接见
事实上,无论是罗斯福还是蒋介石,都选择支持陈纳德的主张。而白修德,则一步步成为史迪威的支持者。
“如果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抓住敌人’,还有保卫你一开始想保卫的东西,一切又将如何呢?如果即使赢了,却输掉了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会怎样呢?”让他产生这样思考的事件是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中,再现了白修德调查河南大灾荒的过程。影片中阿德里安·布罗迪扮演白修德。
经过实地调查,白修德确信,这场大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
一天夜里,在田野里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野里啜泣。他们是一对夫妻,躺在田里,紧紧抱着对方,互相取暖。“在人生的尽头,他们仍然坚守着彼此,躺在坚硬的土地上,躺在冰冷的雪中,他们紧拥在一起,一同对抗严寒,对抗这个人情淡漠的世界。”白修德说这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电影《一九四二》中,有几处无伤大雅的失实。影片中,白修德独自一人探访灾区,实际上白修德是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前往的。关于灾区的照片,由哈里森·福尔曼拍摄。哈里森·福尔曼后来从重庆一路北上,前往延安,写下了《北行漫记》。
白修德的报道最终在《时代》杂志上刊登。时值宋美龄访美,这篇报道激怒了她,并要求亨利·卢斯开除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事后,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到蒋介石接见。白修德给他讲了人吃人的惨状,蒋介石说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人吃人的情况的。白修德说自己亲眼见到饿殍载道,犬吃人尸,蒋介石也矢口否认。最终,白修德请哈里森·福尔曼拿着照片进来给蒋介石看,看到照片,“蒋介石的膝盖因为神经性痉挛而轻微抖动了起来。”
数月过后,白修德接到当地一位神父(《一九四二》中由罗宾·威廉斯扮演)的信件,信中说:在白修德发出电报之后,粮食就经由铁路从陕西紧急调运来灾区,省政府也开始四处开设施粥场,军队也拿出富余的粮食。“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本垒打,第一名的速度。”
此后,除了参加招待会,白修德再也没有得到采访蒋介石的机会。“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对他自己来说也毫无用处,后者的影响更为重大。”
对于蒋介石,白修德坦言自己的看法转变:“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和不屑。”他刚来中国时把蒋介石当作国家英雄,而后来称之为“恶魔”。
白修德认为蒋介石努力地想向西方学习,却往往弄巧成拙。在《追寻历史》中,白修德举了一例:有一次,蒋介石搭乘飞机视察驼峰航线,对机上的降落伞和救生包大感兴趣。他解开了自己的降落伞包,打开了降落伞罩,另外还拆开了救生包。旁边的一位美国军官惊恐地看着他,因为如果遇到飞机事故,他就没有降落伞可用了,那样最后只能由某个机上的美国士兵让出自己的降落伞,意味着总有一个人会无法逃生。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积怨
“中国的麻烦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盟友是个愚昧、无知、迷信、狗娘养的乡巴佬。”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在白修德第一次采访他时,就不惜恶语地评价蒋介石。
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一直贪求美国的援助,而史迪威在蒋介石眼中就是个恶人,总是不断地对他说“不”,拒绝他的要求。
史迪威有强烈的道德感,拘泥于细节和礼节,又有孩子气的固执。这种性格造成他无法理解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却又深陷其中。蒋介石前后三次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终在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中国。白修德是在机场挥手目送史迪威飞机起飞的唯一一人。
史迪威返美同时,白修德致信亨利·卢斯,在长达13页的私信中,告知他所了解到的史迪威被解职的缘由。不过最终《时代》刊发的报道与白修德的陈述大相径庭。
史迪威耿直的性格,也让他与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积怨甚深。
1943年,《时代》杂志要求白修德写一篇陈纳德的封面报道。白修德对陈纳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与史迪威的积怨从何说起?陈纳德回答说,因为“我的那家妓院”。因为他麾下的飞行员常常因为染上性病而被迫停飞,陈纳德派出了一架飞机运送12名经受体检的印度妓女到前线。陈纳德的做法是确保飞行员能够健康出勤,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此事没有获得史迪威的批准。史迪威知道后大发雷霆,陈纳德只好关闭了妓院。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关于战争理念上的地空之争。陈纳德认为空军力量就足以摧毁日本,他传递给蒋介石的信息是,只要给我足够的飞机,你们歇着,我就可以打败日本人。而史迪威坚持认为,必须把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打造成能战斗、够积极的部队。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它们(陈纳德的飞机)将会给日军造成一定伤害,但也将削弱对地面力量的投入,并最终导致地面据点的沦陷。若是如此,那击落几架日本飞机又能有什么鬼用?”
在两个人的矛盾中,无论罗斯福还是蒋介石,都是站在陈纳德一方的。
白修德认为,史迪威让蒋最为惊恐的一点,是他努力和延安建立联系。1944年送别史迪威之后,白修德随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他是随行的唯一美国记者。在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
此行中,白修德发表了《延安印象记》。不过,白修德和赫尔利之间发生争执,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上个世纪50年代,白修德在延安的活动频频被当局调查,乃至他只好远赴欧洲。
在史迪威去世后,应其夫人的要求,白修德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日记》。在日记中,史迪威习惯称蒋为“花生米”。此事为白修德惹来不少麻烦。
老板眼中的“叛徒”
《时代》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中国山东,父亲是在华传教士,他出生后在中国生活了14年。1923年,卢斯和哈佛校友哈顿一起创办了《时代》杂志,成为出版业巨头。
卢斯坚信,中国的命运和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象作为代言人。蒋介石曾经10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宋美龄也有3次。
1941年5月,亨利·卢斯访问重庆,白修德负责陪同,由此建立了两人的友谊,并一起返回美国。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白修德正在《时代》总部的格子间里写报道。卢斯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但卢斯的眼中没有悲伤,他对白修德说:“至少他活到了中美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这一天。”
史迪威事件之后,白修德和老板亨利·卢斯的争执愈发频繁。“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蒋介石的灵魂与目的,这个罪人是有可能被救赎,还是应该被美国所抛弃。”
1945年,白修德被卢斯勒令退出政治报道,与同事贾安娜一起负责奇闻异事的“喜庆”报道。比如贾安娜报道了中国春分有立蛋的传统,发回美国后有人采访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蛋不可能立起来,为此贾安娜为《生活》杂志拍摄了照片,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
为了有始有终见证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白修德必须保住自己《时代》战地记者的身份。
日本投降之后,亨利·卢斯决定《时代》战后头两期要以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交给了白修德,被白修德断然拒绝。卢斯于是命令白修德立即回国。
1945年9月18日,白修德告别重庆,返回美国。“在那一刻,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卢斯的彻底决裂。”
回到纽约,白修德与贾安娜一道埋首写书,原名叫“时间的一点”,在出版商的建议下改名为《中国的惊雷》,于1946年出版,轰动一时。
出版之前,白修德曾将手稿送给亨利·卢斯过目。卢斯认为白修德是在把《时代》杂志当作垫脚石,以攫取私名,称白修德“忘恩负义之徒”。
同年,白修德离开《时代》杂志。
来源:北京晚报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