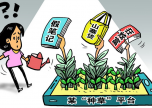为何母亲独自承受这些?一个孩子的故事惹人泪目
我是父亲林金水的孩子,在我身体里住着一个小林金水,一直要到三十岁以后,我才认清这个事实。苛刻,冷漠,易怒,喜欢掌控一切,拒绝任何温暖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还继承了母亲那惯于忍受折磨、软弱(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和悲悯的性情。这些特质时而交杂在一起,相安无事地共存,时而相克,光明、强大的一方战胜黑暗,同样也是强大的另一方,或者是邪恶压垮良善,良善被迫隐藏起来,尽管偶尔也会跳出来无力地反击。
林雪虹

资料图 王金辉 制图
我想母亲身上一定是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这样她才能抵抗艰难、绝望的生活,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不久前,在餐桌上,人俨说起路易丝·布尔乔亚的大蜘蛛,我惊讶地发现它和母亲如此相似。不是境遇的相像,是承受能力和方式的相似。布尔乔亚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个一直低着头,一边修补挂毯,一边默默承受悲伤与痛苦,一个终其一生都坐在缝纫机前,日以继夜地工作,专注的面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压力、与生俱来的坚韧及对宿命的默认。
母亲经常笑,还很容易紧张、惊慌失措。她不是一个沉默的女人。她笑时总是难以抑制地拍打旁边的人,时常笑到合不拢嘴,发不出声音(有一次,马六甲的老三姨来看望她,在餐馆里,她激动得整副假牙都掉出来!)。如今想来,她那夸张的笑也许隐含多重意义,是对生活的幽默和悲苦的回应、反击或消解。那笑很可能深化了我们对她的印象,甚或构成了一个假象,使我们深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乐天知命的普通女人,没有一点隐藏的,更深刻的意义(她到底是不是?是不是?)。
这些年,我渐渐遗忘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漠然,离乌拉港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缘故。我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也在独自面对生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人要承担一切选择的结果”,我总这样想。当小心翼翼的尝试最终都化作一声叹息或被逐渐忘却,不再被提及时,我的这个想法更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她有丈夫,这些事应该由她的男人去做。”我经常这样说。
一天晚上,她突然走进房间,坐在那张我用来顶着房门的圆木凳上。木凳没有靠背,她佝偻着,衬衫的领子耷拉下来,露出她那嶙峋凸出,干瘪、皱巴巴的锁骨。
“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她对我说。
这次她分享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她说起自己在生弟弟时如何差点送命,然后被救的经历。故事中的她三十岁,正在分娩第四个孩子,那是她唯一的儿子。在分娩过程中,她突然大量出血。医生问病房外的爷爷和父亲要保住大人还是小孩。爷爷说要保住小孩,父亲则说要保住大人。结果皆大欢喜,大人和小孩都安然无恙。
她回忆这件往事时,神情是如此淡然。她的上唇很薄,容易使人以为她如果不是在抿着嘴,便是在以一种轻蔑、挑剔的态度说话。她的眼袋沉沉垂着,像两个卧着的,饱满而暗淡的弯月。那个晚上她显得出奇地平静,保持着一致的语调和声线,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更不像是在议论某个亲戚或朋友的令人难堪的事迹。故事说完了,她又继续说起另一件事。
“我有一次想走,下楼后躲在照相馆附近,不知道能去哪里,最后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阿妹已经在台湾了。”她说。
我一直以为她说的“一个孩子的故事”指的是她的故事,那个“孩子”便是她自己。后来,在她的葬礼上,当我对三姨妈说起这件事时,我顿时恍然大悟,几乎可以确定她说的“孩子”其实就是弟弟,是她的孩子。我并没有告诉姨妈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只是告诉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姨妈重复了那句话,以此表示惊讶和好奇。当我也像姨妈那样复述母亲的话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孩子的故事。她的孩子。
如果我当时没有错误理解她的话,我流的眼泪也许不会如此纯粹,而是会掺杂着一丝嫉妒、哀怨、悲愤及失望,这样的忧伤是复杂、沉重的,带着腐朽的味道,让人产生一种很深的挫败感。
我讨厌这种腐朽的味道,厌恶这样的挫败感。
在她逝世前两周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当时她和尤妮在病房里。尤妮是我们雇来照顾她的印尼女佣。那段时间她不是住在大姐的家,便是住在医院里。她有时候会想回乌拉港,有时候会想去某个亲戚家住(她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亲戚会收留她),或是想住在医院的病房里。父亲乐于见她住在大姐家或医院里。也许这是因为他也极度疲惫和厌倦这一切。他迅速将母亲的日用品和药物搬到大姐的家,然后每天在固定时间出现在那里,像在自己的家那样指挥所有人,掌控一切。
“我跟你讲,”母亲以一种明确,但又带着一点惶惑的意味幽幽地说话,“我是要回乌拉港的。那里是我的家。妈妈爱爸爸,妈妈为了你们这五个孩子,所以才没有离开爸爸。妈妈是爱爸爸的。我是要跟爸爸在一起的。我跟阿芳不一样,我是不会离开爸爸的,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你跟大姐讲我是要回家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清朗、平和。阿芳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她正准备和她的丈夫离婚。
挂电话后,屋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绝望的气味。我感到无限悲痛和无助。我原本还应该充满怨毒的。
为什么她独自一人承受这些?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为人子女的沉重枷锁?为什么?
(原标题:母亲,隐忍的蜘蛛)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9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