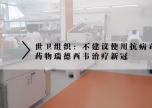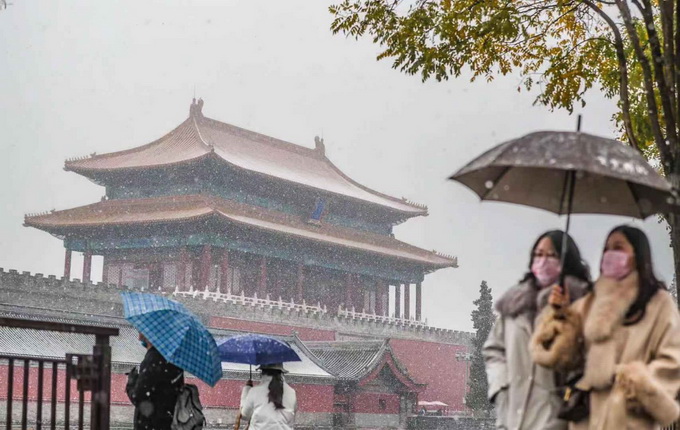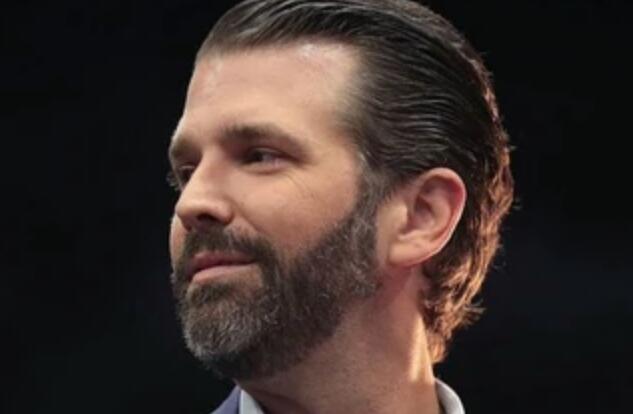宁肯谈《三个三重奏》:权钱性的隔空博弈
2014年11月29日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题材归类,同时根据它来想象小说的成色。那么和权力有关的小说该是怎样的成色?追问它,不如先想想市面上一些“范本”,它们很流行很畅销,也似乎满足了很多人的好奇心、窥探欲,但如果拿它来证明,这就是现实题材的好小说,我只能说,就算了吧。
不知为什么,看一个作家涉足这个领域,总感到他是在碰触一块烫手山芋。那些黑幕道道固然可以吸人眼球,但也似乎让他染上了附着于其间的那种机心、猥琐而肮脏的东西。这是不是这个题材的宿命呢?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看宁肯今年的新作《三个三重奏》,倒是可以确定地说:有。
《三个三重奏》,首发于《收获》,同名出版物刚刚登上新浪十月好书榜。无论是从小说名到封面设计,都无法和这个题材联系起来,但它确是在写权力与腐败,写犯罪分子的逃逸与被审查,还有权钱性的搏弈。权力如果有一袭黑袍,你在书中所能看到的,也就是黑袍本身,但你却能感受到它内部结实的心跳。一个被审讯者的空间,似乎也像诺兰、吕克·贝松电影中那么幻,但这里面直接却映现出审讯者与被审者之间精神的高度对峙。原来如此现实的场景,也可以做此非现实的呈现,一个通俗题材,不可思议地幻了起来。
三个三重奏,回响于三个时空。权力在这中间伸展、变形,既扭曲又充满人性张力。它天然所具有的黑暗气质,仿佛也给了宁肯无尽的想象力。让人吟味其间,也让人时时想到那个古老的文学命题:文学不是写什么,而是究竟怎么写。
一、当现实变得比小说更精彩,当它本身已成为最高的叙述者
“过去我们把权力当成一种他者来看待,是官场之事,和我们老百姓离得很远,但今天,那些侵入市场的毒奶粉、三聚氰胺等,让我们知道,这后面都有权钱交易,权力其实已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和每个人都相关。”
孙:还记得我对你的《天·藏》所做的访谈吗?结束时我说,这部作品太棒了,你恐怕不可能超越。现在看来是武断了,你又拿出这么一部。一个精神气质很高蹈的作家,怎么会想着写权力、性、金钱?这可是另一类作家喜欢的呀。
宁肯(以下简称宁):还是跟《天·藏》有关。那部作品完成后,对我有一种压迫,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后面隐含的其实是:你还能写什么?后来我就觉得,应该走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天·藏》是形而上的代表,那么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呢?肯定是大俗的东西。大雅必须大俗来破。就说到我在这期间的感受:现实生活中的权力与腐败。这种东西,进入21世纪之后,经过互联网的放大与直播,更加赤裸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而且都有戏剧性,以至于让作为小说家的我们都感到无力。
过去老百姓看这些,说谁贪了几十亿,都当个笑话。也愤怒,但会觉得离自己远。现在,新闻不时曝出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之类,你会认识到,这后面有权钱交易。权力腐败已经很深地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就要自问,作为一个当代书写者,你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东西。
孙:其实是问怎样面对?
宁:对。不是说没有小说家面对过,比如那些官场小说之类。也写得很真实,但大家却说它们不叫文学,我就在想,它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孙:你的结论是?
宁:我认为既然是文学,还是要考虑文学的出发点是什么。文学的主体,你不能失掉。这里先不说这个主体是什么,回头看那些官场小说。它们写腐败、揭黑,内幕也展现得惊心动魄。进一步的,也探讨了原因。但这两点即使写得再深刻,也都不是文学上的深刻,而是社会学层面的深刻,新闻的深刻。而这些,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替代。
而《美国往事》,黑社会题材,为什么却震撼人心?不是它揭黑幕揭得深,原因探究得深刻,而是写了成长、爱情、友谊、背叛、宿命,这些都是人性中的东西,和每个人都相通。所以你能看出,《美国往事》成为经典,不是黑社会写得多么好,而是它用黑社会做了一道菜,做出来的是美国往事。而前面提到的那类小说,是用权力腐败做菜,做出来的还是腐败。
孙:一般认为内幕的东西写作者躲不开。但你恰恰把权力里面的这些给抽离了。权力因此就像被罩了一件黑袍,很神秘。这让我想到上月去浙江戴笠故居。那里陈列了很多照片,但都不如墙上的帽子、斗篷往一起一拼,更能凸显戴笠作为特务头子的气质。
宁:你说得对。精气神是最主要的。还不能正面写官场,因为一旦是正面进入,就进入它的轨道。只能在它设定的制约下叙述、辗转,也就被它牵着走了。
孙:而这其实是你最不熟悉的。
宁:是我的短板。我就是再做功课也熟悉不过别人。所以必须独辟蹊径。文学有时需要以实写虚,有时需要以虚写实。在这个题材上,我想以虚写实。这样我才敢触碰这个题材。
二、只有住在小屋的穷人,才知道别墅的价值
“以前的题材就相当于我是在小屋写作,也还挺自得的。现在写权力,我等于来到一个豪华别墅,我发现它给我提供的人性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了,也太有挑战性了。”
孙:三个三重奏,第一组出现的人物关系是杜远方、李敏芬和黄子夫。杜远方是权力中的庞大固埃,黄子夫与他相比,就是个滑稽小丑。但他们同时存在于小学教师李敏芬的生活中,都想征服她。杜远方以静制动,身为她上级的黄子夫是得机会就下手,却屡屡不中。我每次看敏芬和黄子夫的戏,都很可乐,觉得有喜感。因为敏芬不断在心理上说服自己服从权力,但每到跟前,就没法忍受黄子夫亮出的那口烂牙。
宁:这个细节我受的是德国小说《朗读者》的启发。书里的女主人公不识字,但为了掩盖这一点,她宁愿承担所有的罪。在外人看来,这是多么不值当的虚荣,但却是她的自尊所在。小说家就是在这个微小的点上建构起一个人物。非常了不起。
小说中敏芬也是这样。她在主要的部分已经接受了黄子夫的求爱,却在外貌上排斥。而这次要的东西里面,有她做人的底限。
孙:因为通常意义上的主要、次要,是从社会、功利角度来讲的,对敏芬这个个体来说,这个是她的主要。
宁:而在次要的地方守住自己,这个也只有在权力这个题材张力下才能突显出来。
孙:对。换一种题材,敏芬这就叫以貌取人了。而在这里,隐喻的是她对权力的反抗。
宁:这也是我碰触这个题材不断有的惊喜。以前我的小说都非常个人化: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大自然。还没把人投到官场,让他们面对政治、权力这种复杂的东西。现在发现,这些在某种程度更能折射出复杂而丰富的人性。也才能出现后面杜远方、居延泽、李离这样复杂的人物关系。
孙:这个是你的第二个三重奏。同样是两男一女,感觉他们三个人像在对弈,每个人都是以其中一个为棋子,下给第三方看。中间有进退,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惊人表现。
宁:这三人年龄结构很有意思:杜远方比李离大15岁,李比居延泽大15岁。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同时又是情感纠结体。为什么爱而不能,又欲罢不能,这里面还是因为有权力搅和着。权力使人性、人际变得如此复杂诡谲。这真是一个强悍的题材。
孙:当然强悍。以前读《天·藏》,感觉你的语言是玻璃般的光泽,现在似乎都有了像杜远方一样的霸气了。
宁:霸气也是因为,杜远方、居延泽们是权力的代表。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权力掌控一切。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你想这样一个系统打磨出来的精英,那个气场得多大啊。这里面如果有腐败有犯罪,那也是高智商犯罪。
孙:所以你在小说前面引了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一段话: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不过,完美总是得到惩罚:对它的惩罚就是再现完美。”这句话太神了,简直就像是为你这部小说而存在。
宁:事实不是。鲍德里亚这里指的不是权力,而是虚拟世界。讲虚拟世界怎样改变人。我是在写到第一部分之后看到这个。太喜欢了就放在书前。
孙:既然提到虚拟世界,我们就再谈谈你小说中的非现实的幻。微博上我们有过一次私信交流,我说的是:"你把现实处理得超现实,但又在精神层面上高度真切"。这当然指的是居延泽被审讯那部分。那个空间甚至让人想到798,而且为了审讯,你还真设计了一个前卫艺术家进来。那部分太幻了,正是那句:“对它的惩罚就是再现完美……”
宁:审讯这东西太具象,你写得越像,就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东西。所以必须写意。对它进行艺术化处理。学术上经常讲所指和能指。能指在这个题材里可能是审讯啦、逃亡啦之类,但一定要知道,所指是权力。而所有的描述,应该是通过能指,将所指写出来。
孙:也就是居延泽在审讯间沉默不说,他的沉默的支撑是什么。这个通过阅读,读者最能心领神会。
宁:对。这里以虚写实,也是和一般官场小说刻意区别开。面对这个题材,你只有把它的公共性给解构掉,本质才能裸露出来。否则,在这个题材上的文学性、艺术性,还有创造性,都解放不出来。
孙:是啊,你的创造性可真是给解放出来了。
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比,穷人是最懂富人的。从题材讲,我以前是一个住在小屋里的人,当然也很自足,突然有天就来到一座大别墅,发现这里可供审美的东西太多了,而这是拥有它的人意识不到的。
孙:对,连那些写官场小说的人大概也觉得,这东西就是这么一回事,已经不构成审美了。但你在这里,连罪行、连审讯、连男人对女人的征服,都写得构成审美。
宁:读官场小说,你其实很能想到潮水与礁石的关系。潮起潮落,本是最丰富的,但它们只保留了礁石,罪行倒是看得倍儿清楚,但水在哪儿呢?纯文学就是把水写出来。水是什么,水就是人性,是过程,也是审美。
孙:三个三重奏,第三给人物是杨修、“我”还有李南。在这部分你写到了八十年代的北京,相信最能调动起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红塔礼堂的那部分,我还在自己版上刊出过,当时并不知,是为这部小说而写。
宁:这部分最开始没打算写。是在写完杜远方、李敏芬、黄子夫之后意识到的——我需要为整个故事找个叙述人,否则故事和故事间连接不上。于是就有了坐在轮椅上的“我”这个叙述者。“我”饱读诗书,经常做些知识分子形而上的思考。
孙:这个劲头儿蛮像博尔赫斯。
宁:是借用了这老爷子身上的气质,思考宇宙、思考时间,也自我反讽、自嘲,总之有那股知识分子的牛逼劲儿。但我想,不管你多么形而上,如果将你的轮椅推向死刑犯,推向社会,会怎样?于是我就让他身处另一个图书馆——监狱。这也是活生生的书啊,因为每个罪犯身上都有大量的社会信息。而他为什么去,又为什么能去,这里我就必须给出一个条件:他有一个强有力的朋友杨修。杨修和“我”曾是大学同学,现在手握权力。从权力者角度看,“我”整天读书,既不知什么叫社会,也不知道真正的人生,有什么出息。于是就安排他去见死刑犯。一旦找出“我”和杨修的对应关系,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太有艺术张力了。必须将他扩写。写到他的过去。因为他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也是和历史相关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往前追溯。
这个三重奏完全是当背景性的舞台远景在写,但也暗含了我的思考。我们说八十年代是理想年代,是热情的、启蒙的,但实际上八十年代很多问题都悬而未决。比如权力如何制约。你看几年人共同骑车去北戴河,路遇麻烦,最终问题得到解决,还是靠李南的特殊身份。
因为一直没有解决好对权力的制约问题,所以九十年代后物质发达,权力就变得越加畸型。
三、作家和现实,不止是紧张关系。
“作家和现实,不止是一层关系,它同时还要有智性关系、审美关系,这样读者读你的作品,才进得去,出得来。如果仅仅是一种紧张关系,那就很容易形成……对眼。”
孙:对于杨修,你有一句评价:历史是什么,他就是什么。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宁:这是我对杨修这个人物的批判。八十年代,他是典型的理想青年;九十年代,他是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再到后来,他又因为手中权力而犯罪。一个人看来具有每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但恰恰失去的是自我。而在他强大气场对比下的“叙述者”我,尽管时时被他嘲笑、揶谕,但其实是有自我的,甚至,他的自我就是在这个轮椅上建立的。
孙:一个坐轮椅的读书人。这个意象,决定了他是在用特定的视角在看待世间。看来有局限,但因此也显得独特。有的小说写尽世间,情节波澜壮阔,但就是无法被击中,因为你始终找不到它的独特性。
宁:是,它可能是历史,是苦难,但它不是自我。一旦叙述者的“我”和这些重合,就显不出文学的独特性。因为叙述历史、叙述苦难,其它文体也可以做。你做了不能说没意义,但无非是给社会学做个印证。
孙:这个不是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能意识到。或者是从他所表现的题材里面挣脱的。
宁: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个人历史意识一直很弱,或者换句话说,沿着个人历史走的人特别不容易。所以自我非常容易被各种情势淹没或者变得模糊。更多的人是在赶时代的趟儿,都是杨修。而我,最大的优点是自我始终强烈。
孙:这部小说和你以前的《天·藏》一样,小说主体之外还有一个注释空间,能随时把人从故事中拉出来。一部自由的小说,其实又建立了自己的秩序。自己的语言方式。我前面说你的语言很霸气,但其实这里面有进有退,是矛盾的统一。
宁:语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方法。不是往前走,而是在某个地方拐个弯……这里面就有它的味道了。我们总是讲点和点对应,但你有时不妨用面对着那个点。它一定会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你欣赏这个东西,因为你喜欢禅,禅的思维里有这种跳。一跳,就有很多角出来。看现实、看世界、看自我就不是单一的。
我总觉得作为作家,思维与情感的原型不能太简单。简单到我只是要揭示要控诉。一定要对所揭示的东西有所观照。缺少这个,不小心你也就成了它。
孙:但也有人会称赞那种对于现实采取“我控诉”姿态的小说。因为有句话是说:作家和现实要一直保持紧张感。
宁:保持紧张感,当然是必要的,但作家和现实,不止是这一层关系,它同时还要有智性关系、审美关系,这样读者读你的作品,才进得去,出得来。如果仅仅是一种紧张关系,那就很容易形成……对眼。
有时候你在作品中调侃自己,怀疑自己,一切呈现一种开放心态,我执就去掉了。这部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就是这样,他也展现自己局限、可笑的一面,这也是我的自我表达。随着阅读和年龄的增长,人会知道,作为知识分子,你尽可以像上帝一样思考,但也要知道自己并非无所不能。没什么让自己美得不得了,也没什么让你痛苦得不得了……想明白这个,作品才会有多重的可能,也才能让更多的人和你共鸣。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孙小宁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