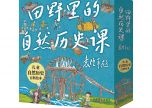2015年5月14日讯,浙江媒体人、作家、摄影家周华诚,去年在微博上发起“父亲的水稻田众筹项目”,他邀请城市人和他一起,用一年时间,跟老家父亲一起种田,并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种田:水牛耕田、镰刀收割、打稻机脱粒。来自城市的孩子全程体验了这次农耕生活。此项计划今年仍然在招募报名中,在新的一轮即将开始之际,本版选发他去年以来陆续记下的种田笔记,希望这些文字,不止是唤起乡土记忆,还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土地,认识耕作的意义。

种田笔记:“该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来的”
周华诚(作家、摄影家)
01 犁田
5月11日。立夏的第五天。
田间:蓑衣,笠帽,一个人,一头牛。
这一幕,就好像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
可惜,村庄里的牛越来越少了。
5月1日,我问父亲,这次能否雇到犁田佬,为我们的大田翻耕。父亲想了想说,有点困难。
我们这片田畈,距犁田佬的家有些远,足有三里地。只我们家一丘田用牛来耕,他得挑着犁、耙、耖等几百斤重的家什,赶着牛,走那么远的路过来,太不合算。
在我印象中,农人肩负犁铧,手执鞭杪,行进在田埂上,是乡间最具标志性的一景。
时至今日,这一景怕是真的要从江南的字典里消失了。
水稻种植,要求大田平整,田泥糊烂,还因要保证灌溉,必须使大田中泥面在同一水平面。水田在耕种之前,要进行这样的一番操作。这是一项技术活。“耕——耙——耖(chao)”这样的水田耕作工序,据说是在唐床时期形成。当时的犁,已很有名,叫“江东犁”。其犁辕短曲,故又叫“曲辕犁”。
在五联,我们没有这样精确的称呼,只是一概称作“犁”。我对比了书上的图片,可以确定,犁田佬现在还在用的,仍然是这种“曲辕犁”。这种犁比较轻便,农人握着犁梢,便可以根据土质情况,随时变化犁田的深浅。而且,我们浙西南丘陵地区,很多田块都不规整,经常是随着山势溪形回转,奇形怪状,边边角角很多,用这样的“曲辕犁”来耕地,就便于人和牛的回转。
耕,是第一步。用犁翻耕,土块被翻过来,荒草就被压到泥下了。水田耕翻之后,还需要灌水浸泡,再把田泥耙碎,于是,第二种工具又要出场了:耙。
耙是一种带木齿,或铁齿的工具,操作时,人就站在耙上,牛拉着耙前进。田泥经过反复的耕耙之后,泥土都已经耙碎,烂成糊糊,这时候还要再进行一道工序,叫做“耖”。
耖,是一种尖齿型的农具,主要是可以把泥面耖平,耖细,也能拌匀肥料。
“两犁两耙一耖”,耕田佬曾经告诉我这样的话。耕田,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以田为纸,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地作画。他们来来回回,在一方方画纸上写下他们的作品。
一场春雨正在淅淅沥沥地下。春雨在水面激起一圈圈细细的涟漪。蓑衣这时候应该出场了。还有斗笠。斗笠滴水,草叶滴水,奏出这个季节最生动的乐音。
我记得小时候,我常常挎一个小桶,跟在耕田的牛和人后面,因为总是有很多的泥鳅和黄鳝被翻耕出来。抓泥鳅和黄鳝,是特别有趣的事情。每次都能拾到小半桶泥鳅和黄鳝!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泥鳅和黄鳝就统统从稻田里消失了。

02 备种
前几日,父亲去县城的种子公司买回了这一季的谷种,包装上写着:“Y两优2号”。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父亲是听了县农业技术人员的建议。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Y两优2号”,在2010年是由袁隆平院士作为中国首届杂交水稻大会观摩现场(浏阳永安镇超级杂交水稻示范基地)的首选品种。
后来有一天,我读《现代中国水稻》这本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培育的稻米品种的名字是——“笹(tì)锦、富士光、星之梦、娟光、火光、一见钟情、大家都来。我们中国的稻米名字是——中优早5号、中优早81、赣早籼37、丰矮占、II优838、冈优22、汕优46、准两优527……我发了一条微博,开玩笑说,“起名字的都是理科生!”
其实中国的水稻种植,历史真是悠久。我们都是食稻之民。我记得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石器时代的顶峰。在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过很多稻谷遗存,而且都是一堆一堆的存在。
原来,四五千年前就有稻香了呵!
03 父亲穿过春天
10日清晨,父亲把谷种放入桶中,浸水。
浸两日夜,水份吸饱,晾起,催芽。催芽两日夜后,可以播种。
所用的种子,要三斤半。一亩田,大约需要一斤三两到一斤四两的种子。
种子播下后,用草木灰覆盖。再用晒干的猪栏粪的碎屑,筛过以后细细的那种,铺上一遍。这是有机肥,能让种子茁壮成长。再用喷雾机喷一道水。
如果天晴,每两天去喷一遍水。
谷芽,一点点冒出来。这时,还要防雀,防老鼠偷吃。
5月15日,谷子下地。
我记得小时候,谷种都是播在秧田中的,并非播在旱地。
制作秧田的要求很高。宋代的农书《陈甫农书》,在“善其根苗篇”中说到,“凡水田渥漉精熟,然后踏粪入泥,荡平田面,乃可撒种。”而要使水田平滑,就要使用到一样农具,叫田荡。
田荡,像一个耙子,来回操持,可以把稀泥水面弄得平滑如镜子。这样,才能把谷种撒在上面。
我记得村庄里曾有人把板凳反过来,扑在泥面上,代替田荡使用。
等秧苗长成,又从秧田中拔秧,移栽到大田中。
而现在,父亲把谷子撒在旱地里。旱地里育秧的好处,是秧龄短、秧苗壮,管理起来方便,移栽大田之后发蘖(音“棵”)快。
父亲这几年都用这样的旱地育秧技术。而我从来没有在旱地拔秧的经历。
我把秧苗发芽、长叶的情形拍了照片发在网上。
马上,就有朋友在网上留言说,到了插秧时,要和我一起下田。
那么,一个月后见吧。
接下来几日,天落阵雨。
父亲听天气预报,说会有一场大的阵雨。他担心大雨把秧地冲毁。傍晚,天色都黑了,他又去田里,用薄膜在秧上覆了一层。弄到很晚才回家。
秧是多么重要的事。秧要是毁了,这田还怎么种呢。
种田这件事,跟老天总是关系紧密。总归还是要看老天的脸色。
这两天,父亲每天晨昏都要去田间走走。他荷一把锄头,穿过春天的薄雾,走在江南的田埂上。他常常会仰头望天,好像是在跟天空对话。

04 插秧,约起
水稻的秧苗长势也不错。父亲去看过之后回来说,再过十来天,可以插秧了。
插秧的时节,一般在秧龄30天左右。早了或迟了都不好。
说好要让杭州和衢州的朋友们带着孩子一起来稻田里玩,我便把插秧的时间安排在6月14日(周六)。借着这样的机会,让孩子结识一下水稻。这样孩子们也就知道,水稻在土地上的样子。同时,也让孩子们一起感受一下劳动的艰辛与美好。
我把消息发出去,结果报名参与的人很多。居然有北京的朋友也来问,怎么走比较方便。我告诉他,先飞机,再火车,然后换汽车,到了县城我可以去车站接他,哈哈。
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上给我留言,有的说很想来。有的说来不了,很遗憾,如果下次有农活,一定要来。留言很多。这也让我吃惊,原来默默关注这片水稻田的朋友们有这么多。
衢州媒体的朋友也说,要给他们留几个名额。当然,这不成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年没有插过秧了。
插秧这个农活,需要一直弯着腰,一边插秧,一边倒退着走,靠着手和脚的配合,把秧苗一行一行地种植在大田中。累。半天活儿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
可是,我想重新体验这样劳累的感觉。站在岸上想,跟自己走到田中间,体会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必须身体力行地去试过,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05 孩子别哭,勇敢踩下去啊
6月14日。晴。
气温三十三摄氏度。
明媚的阳光下,一个孩子站在田埂上哭。许多人围着她,说没关系的,踩下去吧,软绵绵的很好玩。
可是那孩子还是不肯下去。她望着脚边的水田,脸上挂了两串泪珠。
今天是插秧日,前前后后来了三四十个大人小孩,其中有四个家庭是和我一起从杭州出发的。一路欢笑。
那么多车停满了村道。村民都很好奇:你们家到底办什么喜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呀。
插秧的现场也有意思。没这么下田的——戴着墨镜,穿着休闲衬衫,还有的姑娘们撑着花花绿绿的阳伞。知道的,说这是下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海滩上阳光浴刚回来。
一块稻田里,大部分已经插好了秧苗。那是前两天父亲和母亲完成的。现在留下了一片空白,留给这帮城里人来填补。
大家开始脱鞋子,脱袜子。双脚踩到田里,一个个发出惊呼声。
一个小姑娘开始哭,因为“脚踩在泥浆里,感觉很不舒服”。她死活不肯再下田。她父亲在一旁好言相劝,老半天才让她终于尝试着再次探下脚去。
泥浆,水田,对我而言有着多么熟悉的气息。
父亲先带着孩子们在秧地里拔秧,捆成一扎。秧备好后,下到大田,用插秧绳拉直,指导大家靠着插秧绳来插秧。
很多参与者都是初次下田。
有位叫方萱的小朋友,读四年级,她在田里忙活半天,一会儿脸上就糊满了星星点点的泥浆。
几位记者朋友也来亲身感受插秧。问到方萱的感受,小女孩想半天,说又累又热,“农民伯伯很辛苦”。
她妈妈在旁边补充说,方萱和她的同学吴依可一样,只在电视和书本上接触过这些农活,秧苗、稻谷只是在马路边看到过,但从来没有亲密接触过。这一次亲身感受,很是新鲜。
“水稻历来是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对于世代劳作的村民们来说,秧——稻——谷——米,这个过程是再熟悉又正常不过的生命回环,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就是在这个回环的四周敷衍展开的。但是,城市在扩展,乡村在退缩,在这样的一进一退中,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回环却被敲碎成两半。”
这是第二天衢州日报刊出的整版报道中的一句。在这篇《用沾满泥浆的脚向大地致敬》的报道中,还写道:
“这一次,大家都是带着记忆,重新来寻找这个回环的起点,也带领孩子认识这个生命回环的起点。至少,这些来过的孩子们,会知道一粒粒大米是从秧苗上长出来的,至少他们会知道插秧时是不能穿球鞋的,是不能穿着泳衣泳裤下田的。”
用父亲的标准来评价,大家插下的秧苗是很不合格的:有的太密,有的太疏,有的太深,有的太浅。各种情况都有。
等大家插完,父亲又重新下田,为大家的作品“润色”了一下。
但看得出来,父亲今天很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过这块田。如果可以把这块田视作一方舞台的话,以往都是父亲母亲在这里孤独地演出——没有观众。
现在,这方舞台上居然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人。
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父亲说,“现在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都是五六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在种田。年轻人该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来的。”
碗里的饭是怎么来的——这句话讲得好。
在农村,人与土地的感情是很亲近的。这种亲近,城市人无法感知。城市里到处都是钢筋和水泥,想要找一盆种花的土,都得到花鸟市场去买。
你什么时候脱下鞋子,在马路上打过赤脚?
农村孩子小时候,都光着一双脚四处奔跑。
插秧那天,大家光着脚从稻田里走到家里去,结果一个个都哇哇乱叫。因为脚底板被石头子硌得生疼。
疼,以及忍受。
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怕疼。我们也不愿忍受。

06 谢天谢地
6月19日。雨。
6月20日。大雨。
6月21日。大雨。
河水渐满,稻田水位增高。
6月22日。傍晚,父亲用微信发了一张图片给我,那是我们的水稻田——只见稻田一片汪洋,我们刚在一周前种下的秧苗,完全被淹。
忧心忡忡。
6月23日。大雨。
度日如年。只有祈求大雨不要再下。
6月24日清晨,大水终于渐渐退去。秧苗露出头来,重新呼吸。
6月25日。雨停了。
算是老天赏饭吃。
父亲说,如果再多淹一天,这些禾苗就全部要淹死了。
那几天我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稻田被淹的照片发到微信上,每天都有十多位朋友留言,问雨停了吗,问水退去了吗,问秧苗还有救吗,问如果真的被淹坏了要怎么挽救。
如果真的被淹坏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只有拔了,重插。
花费了人力不说,还耽误了时节。
庄稼,是耽误不得几天的。肯定会影响收成。这样淹了几天,也会影响收成。说不定病害也会多起来。
以前,我在乡下生活,常听到农人把一句话挂在嘴上,“谢天谢地”。种了田,真正知道“天”和“地”对农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