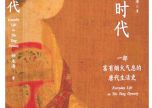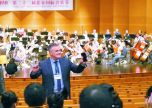2015年11月26日讯,11月21日,台湾金马奖揭晓,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一举囊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造型设计、最佳音效五项大奖,成最大赢家。《刺客聂隐娘》自上映以来,好评不断,同时也争议不断,好评者赞其为“写意江湖、展现大唐古典之美的文化盛宴”,争议者则聚焦于台词的文言化、故事的隐晦等诸多方面。

抛开电影艺术层面的争论,如果我们藉由此片之唐朝意象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唐代,哪些如实,哪些又有误差?记者就此专访台湾禅者、文化评论人林谷芳先生。多年前,他曾以唐传奇的写法为自己留墓志铭,其中后两段颇为传神:“……后,不知所终。某某年,长安肆中,人尝见一老者,须发皆白,冬夏一衲,不畏寒暑,常佯狂而歌,时人以为乃林谷芳者。”而多年以来,他也以这样的古风往返于两岸,致力于禅家锻炼,民族音乐美学,以及古典艺术与当代生命之间的联接。在自许为契于唐人情性的他眼中,《刺客聂隐娘》片中的唐朝,是否就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唐朝呢?
我们能通过《聂隐娘》抵达唐朝吗?
一、依照画来建构唐朝的利与不利
孙:知道您是喜欢唐朝的,而且行文做诗也特别有唐风,若干年前记下您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基本就是唐传奇写法。所以想跟您谈谈侯孝贤的《聂隐娘》。也就是当一个导演调动所有艺术元素来呈现他心中的唐朝时,这里面如实的部分有哪些?哪些还不那么唐朝?
林:谈唐之前先说说宋。当我们从生命情性、时代气象来看历朝历代的话,宋就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宋之前更多阳刚,更多开放性。这样一个社会氛围,或者说生命特质,一直可以上溯到魏晋。也就是在魏晋清谈兴盛时,儒家那些比较名教规范的东西在当时是被摒弃的。
之后南北朝又有五胡十六国,接着就是隋唐盛世,这一连贯下来,近乎有五六百年时间,儒家规范的、内敛的东西在中国都不占优势。尽管从社会结构来看,还是以儒家为本,但就生命情性的挥洒、就宇宙观、生命观的领略,儒家在这期间并不算主流。
但到了宋之后,无论从社会组织乃至审美、宇宙观生命观等等儒家则占有主导地位。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基础认知,我们就不容易了解中国文化的气象之变,也就会把中国文化从单一角度扁平化。
就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待《刺客聂隐娘》的唐代意象,首先能发现,它的意象主要来源其实是画。许多人看这电影会联想到历史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而画又是什么,画本身是一个凝固的静态瞬间,如果没有像陶俑里面人物活泼的动姿相辅助,单从画本身本身来想象真实的唐朝,可能会让我们产生错觉。
而即就是通过陶俑,俑的本身,有些是冥器,也就是陪葬品,还有些所描述的对象是黎民百姓。在我们想要重建一个理想的、比较文人化的唐代形象时,这些也可能被我们忽略,或使不上力。
这样来看刺客聂隐娘,就比较清楚了。它就是从画中出来,带着些文人气息的角度,来看待并重建那个时代的色彩、生活与美学的。
这样的复原,有它的成功之处,比如从服饰、色彩以及建筑空间来看,单从银幕呈现,两岸所拍的古装片中能像这样还原唐代的,基本前所未见。也所以对许多人来说,从这里看到的中国既熟悉又陌生。
孙:为什么说它既熟悉又陌生?
林:因为中国过去拍历史古装片,受明清影响大,顶多有些宋代的影子。像他这样尽心追摹,甚至有些镜头到日本去拍——毕竟有些地方日本还保留了唐朝的遗韵,那样的唐朝的确是我们以前没在片子中看到的。
但如此的唐朝,如果再从生命情性乃至生命观来看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悖反。就是唐朝本身所带有的外放、雄浑特质,并无法在那些静态、凝固的“画面”中给体现出来。
孙:对,我承认那画面是美的,也可能很画面很唐朝,但因为是侯孝贤拍的,他拍东西又从来很静很缓……
林:是比较幽微的、静态的,比较享受一种氛围营造的那种。
孙:这使我又忍不住想到您以前说的台湾文人身上那种明文人气质了。也就是我还是能从他唯美的唐代看到台湾一向的明代审美,
林:可以这么讲。正如台湾许多表演艺术都在这里出现问题。包括无垢、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等,他们的“内敛”不小心会带来气的不畅。
孙:而如果感觉不畅就基本不是唐朝了。

二、唐传奇内部有两个逻辑,那种纠结的刺客不像唐朝的
林:是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这片子拍的是唐传奇。唐传奇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都晓得所谓的大音稀声、大言必简。唐传奇就有这样的味道。气概到了的地方,要么你做挥弘的大史诗,要么就是像禅家般——禅也是唐代的特质之一——非常的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唐传奇就如此,它不像明清的小说那样把什么都交待殆尽。也不会像昆曲那样在一个细部的情感里琢磨。尤其不会有一种……话说一半的感觉,容你去含蓄,让你去琢磨,当然这并不代表说它就没有内涵,它可能意在言外,也可能有所延展,但绝对不是那种静态含蓄的。
孙:我觉得电影本身不仅是静态含蓄,而是情感是尽量往里面收的那种。就像舒淇的悲伤,是洇在手心里哭的感觉。这样的刺客符合对唐朝的想象吗?
林:唐传奇是很短的,刺客的故事也永远很短很短,要理解唐传奇,有两条线需要把握。那里的逻辑其实都简捷,也因为简捷而干净利落。一是报恩这条线,它的逻辑是:他对我有恩,他有个仇人要我去杀,所以我就去杀了。
在这里好一点会交待,这个要去杀的人本身就暴虐,更多是提都不提,所以一般不会出现此人该不该杀的纠结。第二是传奇性。涉及到武功的极致、习艺的过程等。
孙:在这里能看出,侯导尽管拍得很有唐意了,但还是透着些现代思维,舒淇的痛苦也就在这里。虽然她师傅教她的道理是大道无亲,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刺客的任务。
林:我们读古代东西时,首先应该是“以经解经”,再下来才“以今释古”。现代人当然有再创作再想象的权利,这样的好处是让人对自己的处境有广垠的观照和更深的了解,但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你率尔跳过了第一层,在还没有理解它的时候就做解构,没进入那个时代,没深入那些时空中的人的心灵,就以之发挥。就像我们以前谈弘一,当你只晓得俗人的立场,你就无法对弘一弃俗入佛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诠释。
孙:多次听您讲到这个历史题材的再创作问题。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从原点出发,再现经典。不过我发现这个问题评论家考虑得多,作为艺术家,似乎更看重自己的特色。比如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侯导的电影也可以看成,这是他理解的唐朝。他理解的唐传奇的样貌。
林:也可以这样说。这里的确能看到他所认为的刺客伦理,还有人性最后的善良。这些思考都很可贵。但我们一直谈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否由此契入唐代传奇中刺客的心灵。
当代人愿意把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当成脚本来注释,却往往忽略了,古人为什么是这么处理的,它内在的逻辑又在哪里。如果不思考到这一层,我们也就不能理解人类的行为有各种方式,事情给我们的启发性反而不那么大。
人对生命复杂性的观照,很重要一点是来自于设身处地。先理解,再来论它合不合理,但现代人往往忽略前面那个。
所以,回到这部电影里的刺客,也许导演的意思是,我本来就想塑造另一种刺客。但是,即便作为另一种刺客的确形象可以成立,她仍然不是唐代的刺客。
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建构唐传奇中刺客较普遍的生命色彩,通过这部电影,是比较难。

三、语言层面:中国自来,文言分家
孙:《刺客聂隐娘》引起争论的还有台词、对话。有人觉得,银幕上的人物这样讲话比较是古代那个氛围,有些人又不以为然。我个人看时也觉得,刚开始在还没熟悉整个故事时,听这些台词,还是很挑战人的理解力的。这也是片子客观造成的理解不畅。但又很想知道,这样的对白方式,是唐代的感觉吗?
林:中国自来,文言分家。
孙:历来?
林:对,历来都是。你很想象,在过去那个知识不普及的时代,一般人会嘴上挂着呦呦鹿鸣,会讲“窕窈淑女,君子好逑。”懂我意思?
孙:何以见得呢?那时人讲话又没有留下视频音频?我们怎么判断这事呢?
林:一个基本判断是,平常人讲话不会那么精简。因为语言的精简是需要训练的。语言天生是散慢的,所以孔子删诗书,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它精简、美化,而不是当时的民歌原来就是那么精炼的。不信你听听我们现在的民歌,其中会有多少衬字衬词。
中国的文言分家,情况大致可以这样看:老百姓文很少,大白话多些。知识分子“文”多一些,所以语言里有文气。从这个你可以想象,不同时代的不同阶层,讲话大概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文人知识分子,他可能语言里有古意,语词不啰嗦,讲起来有半个文章的样子,但绝不是在念书。
孙:(笑)那您觉得电影电视里哪些比较接近您对古人讲话的想象?
林:大陆电视剧《三国》里在朝廷里讲的那个语言,就比较对劲啊。所谓“丞相明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请丞相不要踌躇……”之类。它换成民间的说法就是: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了,老哥我们就跟着干吧。“这是民间李逵的口气,而放到朝廷臣子身上,就是前面举的这样。
孙:其实看您的《禅 两刃相交》,特别能想到唐公案的语言范式。您的确很唐朝。
林:公案是唐代的俗家话。中国的白话文,和禅家有必然关联,因为那时禅需要用通俗的方式把禅道理说给一般人听,另外也在提醒自己不要死于句下,所以用了这种活泼泼的语言。而这也同时构成了唐朝开阔气象的一部分。
再有,如果你认为唐朝人一开口讲话都这么文言,这么文谄谄的话,那白居易、元稹的那些诗,又怎么可能在唐诗诗林中有那么高的位置呢?
孙:其实关于唐朝,我看过一本外国学者写的《唐朝的外来文明》,我甚至都因此想象,那时的唐长安城,都不是汉人天下。肯定是各色人等都有,说各种话的也都有。气息肯定是特别活的。我对《刺客聂隐娘》的看法是,每一幅画面都是经典,但往一起联缀,又好像缺一些唐朝的大气与活气。
林:你真要谈唐朝活的气息,不止要读唐传奇,新唐书、旧唐书,你还要《乐府杂寻》,唐代段安节所写的那种汉族音乐史论著,你就晓得什么是活泼泼的唐朝。《聂隐娘》的唐代,在我看来还是宋词意象多一些。这里又能看出侯导对唐传奇的不同处理法。
唐传奇虽然精简、利落,但它毕竟是小说。但是《刺客聂隐娘》则的确是诗的拍法。诗可以写成,像杜甫〈七律?咏怀古迹〉中咏明妃那样: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意象绝对鲜明,词也对仗,但这“一去”后的独留,其间已过去三十年。三十年的昭君,生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不需要诗来叙述,诗就是总结。而小说是要铺衍的,唐传奇尽管是留人余思的干净的小说,但它毕竟不是诗。
孙:您将电影比喻成诗、或者宋词,都是很准的,大家也都能感到,侯导并不在乎故事的完整性,他比较在意人物内心的千回百转。一种情绪的暗调调。《聂隐娘》最近在金马奖上斩获六项大奖,艺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起意跟您谈这部片子,也不是为了探讨其艺术的得失,而是想借此探寻一下一个想象中的唐朝与真实的唐朝之间有多少出入。
画面、语言都探讨过了,再问一下,这出戏里的古琴运用,以及片尾音乐的运用,您觉得很唐朝吗?
林:在我看来,就唐朝氛围的营造,用古琴不如用琵琶。我不是写过一篇《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文章吗?讲过这个乐器的特质,据说侯导也曾想过用琵琶,但最后还是用了古琴。我猜想两个原因,一是找不到好的琵琶,二是琵琶的音乐与他整个剧所营造的氛围不搭。
孙:但是他最后的片尾曲听来也很跳啊,全场静,到这时突然很喧腾。据说是一首用布列塔尼风笛加一种类似中国唢呐再加上非洲鼓出来的曲子《Rohan》。
林:你说的第二个乐器可看成管子(筚篥),那个有胡人味道,反而最接近唐朝。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