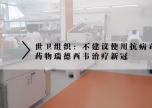年轻作家创作比赛8名优胜者脱颖而出:这是我们的第一本书
2015年7月24日讯,作为“年轻作家创作比赛”的8名优胜者之一,本报记者张逸良的《另一种表达——西方图像中的中国记忆》亮相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
“年轻作家创作比赛”由香港三联书店和新鸿基地产合办,十年以来已经举办五届,共有41位青年创作者脱颖而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从香港到大陆,从澳门到台湾,两岸四地几千名写作爱好者加入到比赛的行列中来,用自己的文字和创意,随心出发,向内心世界和时代进行探索,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同众人分享。“第一本书其实给了自己一个历练与反思的机会,也为自己的成长留下了一份证据。或许它并不完美,甚至还有着很多遗憾,但这毕竟是个开始。”
法国的《小日报》曾经是法国社会重要的传声筒,在十九世纪末发行量达到百万份。《小日报》曾经用大量的版面和新闻图画报道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张逸良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两次赴法国寻找,集齐了散落在一千多份《小日报》之中近七十段中国故事,并于去年参加了此次创作比赛,迎来了第一本书的出版机会。关于张逸良和他的《小日报》的故事,《书乡周刊》在5月份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当我在三联韬奋书店看到这个比赛的宣传海报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今届8名优胜者中的一员,并在2015年香港书展首发新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将自己平日一些零散的图像琐记整理起来寄出,没想到在几个月之后收到通知进入复试,并最终可以将它出版。四年前,我闷在大学宿舍里对着那堆法国老画报发呆冥想,随手记录下我看到它们时的心情,其实就是个闲散记录。而当四年之后,当我刻意去把它们按一本书的间架结构来进行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文字本身也需要经营,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这也成为我此次编书过程中的最大感悟。”
本次比赛的主题是“发现”。在张逸良看来,他和其余7名优胜者的第一本书都是建立在发现这个主题上的。年仅13岁的台湾小作者迎曦,亲赴台湾东部的兰屿岛调查走访,将岛上达悟人与大自然共生共存的故事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香港设计师汤文舜在创作时刻意将人与动物的角色颠倒,藉此为动物生存状态发声;个人与时代的青春记录、香港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徘徊生死线时的生命自省等话题亦成为优胜者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发现身边的人与事,还是发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或者仅仅是去发现自己,这本身就体现了写作一个最重要的来源,便是注意到生活当中这些琐碎而微小的细节,并能从中找到它们与自身经历和学识的交集。”
书展进行时,部分优胜者参与了“年轻作家创作比赛作品点评”讲座,与观众分享写作时的新发现。张逸良也采访了这些善于发现的同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作品的缘起,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坎坷与挫折。
芊祎:也许我们就是 “阿怪”

“阿怪”是芊祎的一个亲戚,也是她绘本的主人公。很多认识“阿怪”的人看过之后,都会觉得这个“阿怪”和他们认识的那个人太像了,尤其是那双永远举在胸前的手,指甲很短、胖胖的,干净异常。
这个名叫“阿怪”的胖女人是个医生,终身未嫁而且极度洁癖,她用自己独特的视角颠覆了我们对种种生活常规的定义,也因此引来了家里人的议论和忌惮。在家里人看来,“阿怪”很怪;在“阿怪”看来,所有人都很怪。
“阿怪”很怪——城市污浊的空气,让她提心吊胆,生怕那些微小的颗粒物会在她的肺里作怪,引发种种可怕的疾病,纵然所有人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她时刻要戴上口罩,受不了一点尘土,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泡在浴缸里;消毒水喷壶是她的“忠实伴侣”,连敲笔记本键盘都要用一双竹棍代劳;对于别人的善意,她总会拒绝,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哪怕是要扶她一把,她都会害怕有细菌沾到她身上。
不过在“阿怪”的眼中,所有人都很怪:为什么所有人无时无刻都拿着手机,一到吃饭的时候还掏出来一个劲儿乱拍?商店里的东西就那么有吸引力,引得人们大包小包,为此忘乎所以?为什么人们都要很晚才睡,早上赖床不起?细菌无处不在,怎么能够如此不当回事?
看到“阿怪”,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接触到的那些行为略显怪异的人,在他们的世界当中,这些作为再平常不过,因为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有着同样的习惯。而一旦脱离他原有的认知境域,一些人的行为更新他的想象,他就会产生异样的感觉。顿时我发现,“阿怪”这样,确实也有原因。
视角不同,也就有了区分。正如芊祎所说:“我们或许都是‘阿怪’,那些早已被我们忽视的细节,或是某些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又何尝不是一种怪呢?”也许“阿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抑或就住在你的心里。
直到现在,“阿怪”也还不知道有人在画她。芊祎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理由去告诉她,因为“阿怪”并不会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画。
钟玉玲:想控制自己的身体 并不容易

一场重症肌无力,改变了钟玉玲的人生轨迹,万分之一的患病几率,让她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两年时间,流转于各个医院和科室,眼见旁人的生与死,思考的同时也在用文字记录着。
“疾病是最好的修道院,走进去的人都会成为最虔诚的教徒”——《疾病王国中的身体生活》正记录了她经历的这段日子。她说这本书就像是“一个生命体在疾病的阴影之下身体与精神对话以抗击痛苦之旅”,处处都是入口,像一个思考的迷宫。
从患病这一刻,钟玉玲便感受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身体变化,惶恐、无助、伤心、愤怒,千百种情绪在她心里纠缠,纵然如此,她只能选择面对,时刻又想把自己藏起来。
躺在床上两个月后双脚的第一次着地,让钟玉玲几乎跪倒在地面,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她开始用心去感知身体,并试图重新掌握对身体的控制权。
生病的日子漫长而焦躁,疾病面前,想控制自己的身体谈何容易。失眠的夜晚,钟玉玲靠着想象食物的味道入睡:每次妈妈探病时为她变着花样做饭,是为数不多的生活味道。平静只是短暂来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发作让她陷入休克,双手无意识地撕扯,为了避免在气管插管之后引发条件反射,医生使用了束缚带。而此时的她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眼前不断闪出金黄色和桃红色相间的万花筒图案,等到再次看见刺眼的灯光,她想喊声“妈妈”,却根本说不出来:“那时的自己就像‘冰箱里的猪肉’一样,动弹不得。”
虽然钟玉玲在手术之后没有用镇痛药,但护士总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她痛苦的呻吟。插管手术遗留的伤口不理想,八针局麻的小修复手术刚到了第四针就已无法避免疼痛,针刺进皮肤,在肉里穿行,但她没再选择麻醉,因为疼痛根本无法避免。
若不是生病,也许钟玉玲不会细细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胸口下的那条铁丝,似乎已经与胸骨连成一体,但异物的入侵却让身体这个有机的系统多多少少产生些改变,“虽然生命可以挽救,身体却很难治愈。”
关嘉利:别样的“七年之痒”

七年是个坎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七年是关嘉利同香港之间发生的故事,七封写给同是新移民苏伊的信,透露出她来香港生活的种种境遇和感受。
2006年,关嘉利与父母移民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新移民”。那时候,她草草结束高一的学习,与十多年来熟识的朋友与生活告别。面对新的朋友与同学,新的生活与学习,挣扎、迷茫与彷徨时刻相伴,她与新生活的接轨并不顺利。
在广东开平,关嘉利的故乡,她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三层高,还有田地与小花园,在香港却是天壤之别。全家收入不高,住的是政府的公屋,六七口人住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没有独立的房间,只是用铁线拉一块布帘就当作间隔。入学也令她烦恼,关嘉利需要降一级插班学习,她的英文不好——初一开始,她才学ABC,而那时候全班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系统学过英文,这也让她受了不少同班同学的脸色与嘲笑。
为了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关嘉利必须熬过那几年,而那几年恰恰也是她人生中转变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她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去爱尔兰做交换生,试图换一种视角来看待香港,从而尽快融入到那个新的环境之中。渐渐她发现,香港并非她初来乍到时所碰到的那般无情和冷漠,每个人只顾看脚底下自己的那条路,其实也有着互帮与互助精神:做义工时,一些陌生人怕她晒着,一个劲儿让她到阴凉的地方去;一次因为身体不适,差点儿晕倒在火车里,一个阿姨扶了她一把,送她到客户服务台;下雨的时候被堵在地铁站口,一位不认识的姐姐问她要不要去小巴车站。
七年之后,关嘉利正式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夫妻之间尚有“七年之痒”,更何况一个在故乡以外的地方住了七年的“新移民”。但关嘉利说:“如果七年之痒是一种感情或者感觉从有到无的话,我觉得在香港的七年刚好是相反的,应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然,跟七年之痒一样,都需要通过一些考验。我在香港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初的想回去又回不去,到现在的想留下好好生活。”她也坦陈新移民这个身份特别尴尬,也很特殊,香港本地人会把她当作内地来的人看待,而内地来的人却会把她当作香港人。
如今她还会每年抽出时间回到开平,故乡也在经历着剧变:大多数年轻人都搬到城市里居住了,乡村里只剩走不动的老人,冷清而陌生。开平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游人也多了,但变得浓妆艳抹起来,少了几分朴素,伴着她一丝淡淡的隐忧。
李佩珊:打口碟上的复刻青春

“从头重拾身边琐碎,从头重拾某印象,从重重叠叠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二十多年前达明一派《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香港流行文化在懵懂的中国暗自游走,成为李佩珊难得的青春记忆。
几年前为完成学校的期末作业,李佩珊选择了港台文化这一她十分感兴趣的选题,并在保定走访调查。她第一次看到打口碟是在家音像店里,老板是个中年人,自己喜欢捣腾碟片,留了几张打口碟当个念想。
不少“摇滚老炮儿们”都说,“打口”是他们与摇滚乐的第一次接触。达明一派的歌、周耀辉的词、周星驰的电影,国内匮乏的文化工业正在自我炫耀地延续着自己的出版事业之时,这些被称为“洋垃圾”的欧美港台碟片,却让无数城市青年第一次感到与世界的同步,虽然这只是在边缘的徘徊,带着些许叛逆和不入流,却仍旧成为不少人的青春记忆。
然而李佩珊没有这段经历,九零后的青春并没有像八零后那样浓重的时代印记,所受的文化熏染混杂而迷茫,也注定与那个波动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忆——杨波一篇《打口是一道伤口》以及豆瓣上Rockduan保卫音像店的活动,才让她对“打口”有所了解,并开始沿着一些老玩家的足迹去寻找打口碟。数字音乐统领的天下,下载和复制出奇方便,属于打口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找寻的过程并不容易。
“十多年前打开电视机,多多少少都能看见香港电视剧和电影,徐克、王家卫、周星驰,那香港文化输出最厉害的时候。”李佩珊是在那时对香港文化有了初印象,而这也成为她十几年后去写作时的起点,由此延伸到地域文化的流行以及世情人心的观察。
李佩珊说她的青春一直在“复刻”,重复着别人的故事,同时又带进去点儿悲观和仰望的情绪。虽然香港文化的影响力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些东西却很难改变,“就像这打口碟,现在也许放不出声音、损坏了,但经历过这段故事的人一看见就会感到亲切,那种感觉是刻进骨子里的。”
艾文:理性与包容 让世界不同

艾文通过“优才计划”来到香港,在香港打拼了一年多。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工作之余到智行基金会外展干预小组做志愿者,每个星期都和其他志愿者去各地做一些宣传。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开始与一些同性恋者接触,对这个群体有了更为深入和真切的认知。这些人所经历生活的种种不安和痛楚,尤其是当面临旁人与社会的歧视与不解,让他们一度绝望,也让艾文触动。
十几个人,构成了《世界已经变了》这本书,艾文说他们的活法儿就像是鸵鸟,平日里低着头一个劲儿乱跑,风沙大了干脆把头埋在沙子里,“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活法,也是一种最无趣的一种活法”,毕竟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如此,一个渺小的个体改变不了什么,更不可能用自己做赌注,选择去承认,去勇敢做自己。
如果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重新来选择一次,他们还会不会这样做?
艾文对一个叫“巴黎”人印象深刻:“我去过‘巴黎’在西单一个老四合院的家,简陋而阴暗。和他聊天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挂着的他年轻时的照片,有点恍惚了,仿佛看到他几十年前的潇洒。如今他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不求吃穿,痛痛快快活着。”从原来的“巴黎小姐”到如今的“老巴黎”,从优秀的青年模范教师到靠卖地图和吃低保过活,“巴黎”的一生起伏跌宕,也见证了社会对于这个群体认识的变化。1986年“巴黎”最后一次走出监狱,人生的黄金十年,他三次被捕入狱,有六年都是在劳改农场里过的,即使在监狱,这样的身份也倍受歧视。
“当我从巴黎家里走出来,看见现在这片天空,突然我觉得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或许这个时代的理性与包容并不深刻,多少存在些不解与歧视,但毕竟是开放多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儿法,自由是自己给的,改变自己,也就是改变了世界。
来源:北京晚报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