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胶东这片土地在革命战争年代竟然发生了那么多悲壮而传奇的故事,随即开始着手搜集资料。真正让我们下决心要深挖这座庞大矿藏的原因,还是题材本身具备的对一个作家的魔力。作家遇到一个好的题材,应该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据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观察,目前尚没有一部在国内产生影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工作多少带点填补空白的意思。

《烈火芳菲》 铁流 赵方新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等渐渐深入下去,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块多硌牙的“硬骨头”!胶东革命史所包含的内容,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经过审慎的研判,决定采取段落式结构来建构本书,即选取胶东革命史上有代表性的阶段和事件,表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此书不可能是全景式的叙事,只能是局部叙事了。即便如此,素材的裁剪还是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精力,特别是对那些很“有料”的素材痛下杀手时,我们何其心犹不甘啊!最后,我们选取了“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和乳娘群体为主要内容,约略对应着胶东革命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
这种安排,造成了本书的一大景观:在胶东革命的舞台上,前半场男性为主角,但也不乏女性的参与,后半场女性为主角,也兼顾男性的戏份,他们刚柔相济,共同绘就了一幅血火奔涌、荡气回肠的革命画卷。
如何讲好“胶东革命故事”,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报告文学的根本是真实性,我们的叙事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在不少场合听到读者诟病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差,有报告而无文学。是啊,确实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时,出于偷懒的原因,或缺乏熔铸功力,随意堆砌材料,肆意引用摘抄,导致作品面目僵硬,令人一见生厌。这怪不得读者,只能怪作家自个儿不争气。基于这种认识,就给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写出有生气的人物、热腾腾的故事来。
有人曾经问沈从文先生如何写好小说,他告诉人家“贴着人物写”。这确实是写作的不二法门,作者跟笔下的人物有距离感、疏离感,走不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很难把这个人物树起来的。而故事是跟着人物走的,解决了人物的问题,故事自然带出来了。向人物无限靠近,是创作上的华山一条路。为此,我们不得不做一名掘进者,从芜杂的资料和厚厚的时光壁垒间开出一条隧道,抵达人物面前,倾听他们的吆喝、絮语、歌哭,感受他们的气息,与他们俯仰于山海之间;或者做一名探访者,走进人物生活过的环境,触摸他们遗留的气息,寻觅蛛丝马迹……
张静源,作为统一的胶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闪烁着强烈的人格魅力。关于他的故事散见于多种回忆录,他所经历的事件因遥远而迷离,甚至混乱。我们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爬梳和琢磨,一个意志坚定、信仰崇高而又带着青涩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清晰起来。张静源投身革命之际,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之时,共产党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境地,因而,他是抱持着一颗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参加革命工作的。毋庸讳言,他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幼稚、轻信、冲动、忧郁等缺点,恰恰是这些因素的出现,使张静源这位革命者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当他得知莱阳县出现了两个“县委”后,立即忍痛别妻辞子,只身赶往事发地。他面对分裂分子徐元义自立山头的作为,毫不畏惧,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徐元义表面接受了党组织的整顿后,张静源掉入了“轻率的泥沼”:他不听同志们劝阻,前往徐元义的老巢跟其会面,惨遭谋害。这就是书中《牺牲者》一节的故事。在这个悲剧背后还衍生出一个悲剧故事:他牺牲后,妻子带着幼子彷徨无依,孩子很快夭折,她也陷入乱世的困苦……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在当地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威海市文登区僻远的阎家泊子村,七拐八拐,找到了一处农家小院。这里便是烈士刘福考的故居。里面的屋子里陈设着几件跟刘福考有关的物件,似乎在提醒着我们曾经发生的那个惨烈故事。
“一一·四”暴动被敌人镇压后,反动势力疯狂反噬革命群众,为打击敌人、宣示党的力量的存在,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策划了一起除暴行动。行动结束后,在撤退途中跟敌人遭遇,红军游击队员刘福考主动殿后掩护,他在同敌人周旋中腰部和腹部中枪,后被进步群众护送回自己家中。他自知活不了了,就央求父亲用绳子把自己勒死,免得沦为敌人的俘虏。悲痛的父亲下不去手,就把他藏到了村外的玉米地里,放下两块干粮走了。敌人“清乡”过后,父亲赶紧去找儿子,后在一眼枯井里发现了刘福考。他想法拉上儿子来,此时的刘福考已经神志不清,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用最后的力气央求父亲成全他。绝望的父亲只好在一棵树系好了绳扣,头不回地走了。刘福考挣扎着爬上石垛子,自缢身亡……这个悲壮的故事久久撞击着我们的心扉,隔着遥远的岁月,依然让我们感动于那一代革命者对信念的忠诚。
而此后的故事更令人为之唏嘘和赞叹。
刘福考牺牲后,她的妻子王淑贞已经怀了八个月的身孕,一悲而疯,整天疯疯癫癫地四处跑。人们看着她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尽管她已成为人们眼里十足的“大疯子”,可是刘福考送给她的定情之物——一串珠花,却始终稳稳地戴在头上。解放后不久,王淑贞的身影出现在一次表彰大会上,她披红挂彩,珠花映面。人们这才知道,她一直在以装疯卖傻的方式作掩护为组织送情报。现在老人家依然健在,平淡地生活在这座小山村里。这对革命夫妻的故事,不需要任何渲染,就那般震撼人心。我们驻足在英雄牺牲的小村里,耳边响起了阵阵枪声,一个血污的身影走出暗淡的历史走廊,向着熹微的地平线坚定地走去……
无疑,如果能直接接触到人物,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自然弥足珍贵,但这种机会太渺茫了。不过,采访他们的后人确实能弥补一些遗憾。我们在书写乳娘的故事时,在乳山市的山区进进出出,拜访了许多乳娘的后代,这些后代作为乳娘的代言人,具有无可怀疑的合理性,正是在他们的述说里,我们获得了一个个饱满的乳娘形象。
在一个豪雨如注的天气里,我们在乳山市一个山旮旯儿里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宫培爱老人,他的母亲戚永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名乳娘。经由他的讲述,我们慢慢走近了那位性格坚毅、情怀深沉的母亲。
宫培爱讲到的一个细节可谓“闪闪发光”。戚永江像大多数乳娘一样,对抚育的革命乳儿比较偏爱,甚至是溺爱。有一天,乳儿金枝在一户人家玩耍时,女主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惹哭了小金枝,她跑到戚永江跟前哭诉,戚永江也不问明白事由,拉着金枝跑进那家人家院里,就跟那个不识相的女主人打到了一处,啪啪扇了人家好几个耳光……这样的细节就像土里的金子,只要一个就足以使人物熠熠生辉了。我们写到的乳娘的故事,大多就是这样从大山深处被我们挖出来的。宫培爱本人也参与了乳儿金枝的成长,跟金枝结下了深厚的兄妹情谊。同时他个人被冤枉为杀人犯,蹲监狱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乳娘故事的河流里,成为一朵旁逸斜出的浪花。不得不说,正是宫培爱本身的参与,使这位乳娘的故事具有了复杂的内蕴,氤氲出另一种悲剧的氛围。
我们在写作《烈火芳菲》时做了一些探索和实验,而其产生的效果,还需要读者加以印证——那么,就请您打开这本悲壮与柔情交织、回荡着山海之音的书吧。
(原标题:向人物无限靠近)
来源:北京晚报 铁流 赵方新
流程编辑:u028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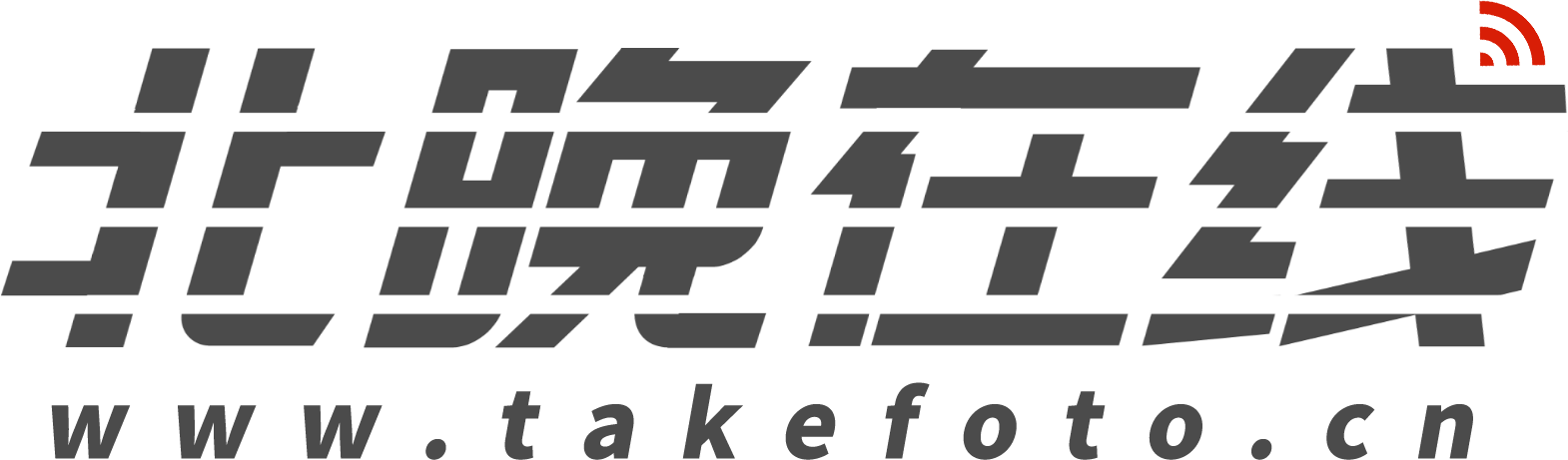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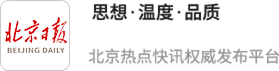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全部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