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铁凝的相识始于30余年前的一次采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坛,铁凝属于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1983年,《哦,香雪》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1985年,《六月的话题》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分别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村路带我回家》等两篇小说也被改编成电影,各种采访、邀约纷至沓来,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是相当忙碌的名人了。
我所在的《中国文学》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刊物,我们自然注意到了铁凝的创作,先是选载了她的两个中短篇小说,准备以“女作者作品专号”的形式隆重地向海外读者推出。因为要配发相应的介绍文章,编辑部便派我到河北保定对她做一次专访。
那一年铁凝刚满30岁,是我所采访的名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
虽然已是声名鹊起,但铁凝显然是一位沉得住气的作家。我来到她家的那天下午,她正在写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玫瑰门》。因为想要把计划中的章节写完,所以等到她终于搁笔出来相见的时候,我已经在客厅与她当声乐教授的母亲聊了好一会儿。“成如容易却艰辛”,借此我也了解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生产”过程。
一
初见铁凝,你会很自然地被她那双明亮有神、顾盼生辉的眼睛所吸引。在作家圈里,铁凝是一位公认的美女。用台湾作家林海音的话说“眉是眉,眼是眼”。据说作家谌容与她同住时特意做过检验,近距离观察过她洗脸的情形,证实她没有用假睫毛来装饰,美目完全“出自天然”。
铁凝爱美,平时很注意自己的穿着。有一次她穿了件白色的呢绒短大衣来见我,看上去非常优雅出挑。我立即夸她衣服好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件衣服可花了300元呢!言下之意有些心疼。确实,在当时,这个价格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偏高的类型。但因为穿着实在好看,她的心中也便稍稍有些释然。由此她跟我说起一件旧事,以证明挣钱的不易:在北影招待所为自己的小说当编剧时,实在是觉得寂寞又辛苦,几次想过放弃,但为了那5000元的稿费,最后还是咬咬牙忍了。

铁凝在选用“作者照片”时,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事先都会反复斟酌,力争体现最好的审美效果。记得当时她曾寄给我两张照片:一张准备用在杂志上,是参观画展时所摄,黑白生活照,长发飘飘的形象,很清纯;一张是站在水仙花旁边的彩色照片,穿着件漂亮的绿衬衣,色彩、构图都恰到好处,表情也很生动传神,准备用在英文版小说集的封底,她特意在来信中注明一定要按她剪裁好的构图制版。因为喜欢,这一张彩照后来在她的不少集子中都出现过。

二
长年生活在河北的铁凝,其实出生在北京,住到4岁才回的河北保定,后来因父母去干校又被送到北京的外婆家,在西城区的小胡同里住了几年,这也是后来她的小说常以北京为背景、经常会写到北京胡同生活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名作家,铁凝既感谢生活对她的馈赠,更感激曾经对她奖掖有加的前辈。与许多才华横溢但成长艰辛的作家相比,铁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在写作之初就得到了名家的推许与鼓励。正是他们别具的慧眼让铁凝顺利地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其中一位便是以《小兵张嘎》名世的徐光耀,另一位则是《荷花淀》的作者孙犁。
当铁凝在家里兴奋地念她第一篇用小说的方式写的作文《会飞的镰刀》时,她的画家父亲铁扬欣喜之余立即带她去拜访了他的好友——著名作家徐光耀先生。
徐光耀先生的一句话“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成了铁凝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她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作家梦,立志当中国的“女高尔基”。
当作家要有生活,高中毕业的她义无反顾地去了河北博望县插队,当了四年地地道道的农民。当她的农村女友捧着她带有十二个血泡的手心疼得落泪时,她的心里是骄傲的,尽管在她后来回顾这段生活时把自己当时的举动概括为“真挚的做作岁月”。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丰厚的生活为基础,所以她在后来创作“三垛”系列(《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时显得那么的底气十足。
1982年铁凝创作了短篇小说《哦,香雪》,但这篇在后来为她带来巨大声名的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最初也未能入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备选篇目,是老作家孙犁的赞赏与肯定为小说带来了转机,也由此改变了铁凝的文学道路。
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写道:“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这已经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了,这是发生在老作家与新作者之间意义深远的一段佳话,流露出的是孙犁在面对一棵文学幼苗时由衷的欣喜与呵护之情。每当提及此事,铁凝都是满心的感激。
三
铁凝是一个很重视细节的作家。
她的小说中常常有令人赞叹的细节表现,如《省长日记》中的这段:
前进袜厂几十年如一日地生产一种“前进”牌线袜,这种袜子穿在脚上透气性能还好,可是你一开始走路它就开始前进,它随着你的步伐,慢慢从脚腕儿褪至脚后跟,再褪至脚心最终堆积至脚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脚上旋转,平白无故的,这袜子的后跟就会转到你的脚面上来。如若这时你恰好当众抬起了你的脚,谁都会看见你的脚面上正“趴”着一只脚后跟。这可像个什么样子啊,它呈现出的怪异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发现某个人的后脑勺上正努着一副嘴唇。
她在写作中重视细节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如此。
英文版《麦秸垛》出来后,铁凝专程跑到北京来取我代她购买的上百本样书。当时她是与她的父亲一起到我办公室来的,还特意带了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送给我,她的体贴让我很是感动。
我注意到,铁凝在网上发布的个人简介里,在提及她的作品时会特意写上出版社名,在海外出版的还会加上译者名,非常严谨细致。这一小小的细节包含着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体现出她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段时间因为计划出版一本中文版的“铁凝精短小说集”,我们俩通过写信和电话沟通了很长时间。虽然由于某种人为因素此书最终未能面世,但当时筛选篇目、商讨内容时兴奋热烈的场景依然如在目前。
每当有新作面世,铁凝总会及时寄给我,在扉页上写上些“批评”、“指正”之类谦虚的字眼,我这一方呢,也总是关注着她的创作情况,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把她的优秀作品译介到国外,那时候我会体会到作为编辑的幸福。
四
2001年,生长了49年的《中国文学》被迫停刊,因为原先我们拥有译文版权的一些作品要转移到另一家出版社,需要和一些老作者打招呼,我负责向曾经合作过的作家一一写信征求意见。铁凝对此事很重视,特意从河北打来长途电话,我一开始没有接到,她便跟我的家人留言说“我是她的一个作者”,她谦虚低调的行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2007年,我因一本参与责编的图书获得鲁迅文学奖,受邀前往绍兴领奖。在颁奖现场,我与已担任作协主席的铁凝又一次相遇了。

本文作者(左)与铁凝合影
距离上一次见面已有20年的时间,我们都已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当我在一旁看到被作家们包围的铁凝,心中不免有些顾虑:经历了种种变化,有了新身份的她还会记得“从前”吗?毕竟有太多的人都会“事过境迁”啊!待到她与众人握手寒暄过后,我走上前去试探地问铁凝:是否还记得我这个编辑?没想到她马上说当然记得,并且立即喊出了我的名字,接着便与我热情地拥抱,关切地问候这些年的情况,完全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因为高兴,铁凝一边说话,一边还与我牵着手走了一段路,直到走到颁奖的通道才与我告别。
2010年,我因编辑《对话:中国模式》一书与铁凝再次有了工作上的联系。这本书是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与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的对话记录,单位领导想邀请各方面具有权威的名人写推荐语,因为知道我跟铁凝的关系,他们就想让我出面去请。本来我是不好意思去麻烦铁凝的,尽管她曾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她”,但我知道她平时工作繁忙,好不容易有点业余时间得赶紧投入写作,因此不想拿这件“小事”去打扰她。赵启正知道后巧妙地用激将法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我试着给铁凝写了一封邮件说了我们的想法,没想到她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很少为这种“新书推广”写评语,由此可见她是很顾及了多年的交情。
样书出来后我去向她面谢。我与她约好在她的作协办公室见面,这时距上次在绍兴见面已过去了几年时间。她见了我第一句话便是:“你烫了头发,我结婚了。”以此总结我们俩在生活中的改变。她没有把结婚视为了不得的大事,只是觉得缘分到了,也就结了。她甚至曾专门提及她跟先生都喜欢晚上喝粥这一“共同的爱好”。真是个注重细节的作家啊,我在心中不由得感叹。她所强调的这一“共同的爱好”在别人眼中也许只是个小小的习惯,但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习惯意味着他俩的契合程度,日常相处的自然与和谐。
跟铁凝说话,你会很快忘记她的官员头衔,因为她关心的是文学,她牢记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我自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她的创作,我们聊天时也多是作家、作品的话题。临别时,她特意为我挑选了一套人文社出的九卷本《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同时为我签上名字,再次写上“批评”之类的谦词。我看到那不变的字体(其中“铁凝”二字就像行进中的两个人,出头的笔画齐齐向着右前方,颇有奋发向前的含义),不由得会心地笑了。
铁凝曾在她的英文版小说集《麦秸垛》的序言中说,她写作的初衷是因为对这世界“有话要说”。

铁凝小说集《麦秸垛》英文版封面
她是通过一部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她的诉说可以说是滔滔不绝。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已经出版了《玫瑰门》《大浴女》等4部长篇、《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作品,总计400多万字。
我想,在她强烈的诉说欲望里,一定也包含着向世界传递人间的温暖和心中的感动吧。
(原标题:铁凝的细节)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钟振奋
流程编辑:L021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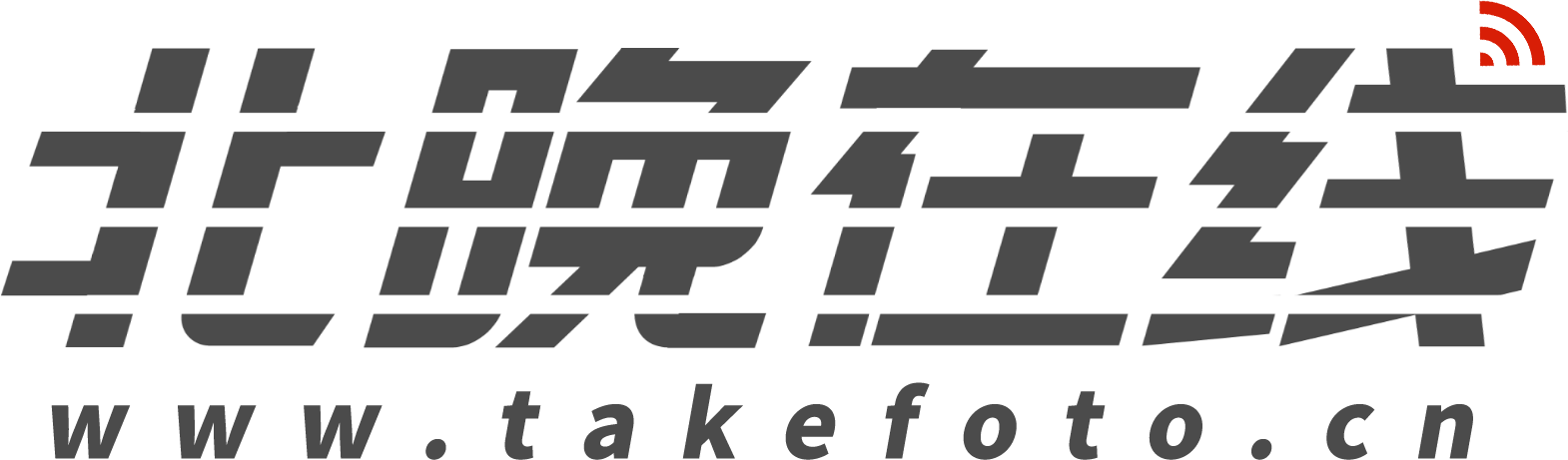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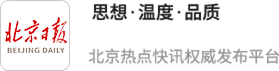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全部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