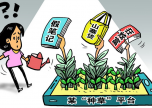日本电影史家来京讲日本电影:日本观众心中的高仓健,和你们的不一样
4月22日,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作为一场影迷的狂欢,“春天到北京,看最好的电影”已经成为它最强有力的召唤,将万千的影迷吸引到大银幕前。这其中的“日本电影”单元,已经形成它特定的观众群。不过,你即使已经通过电影节,看过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等巨匠级导演的影片,也还熟悉当今国际电影节拿奖拿到手软的是枝裕和、河濑直美新片,但是对照日本电影史家写就的日本电影史,仍会发现,这中间有很大的空白地带。说到底,那些大师新锐们的电影,还只是日本百年历史中的冰山一角。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电影史家四方田犬彦先生写就的《日本电影110年》在电影节之后阅读,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著述者是通过历史进程来梳理日本电影,而且在于,它能让人从不同维度思考,什么是日本电影。
作者: 任川

借鉴日本影片《带着吉他的候鸟》拍出的台湾电影
受到日活电影影响的港片《英雄本色》
牧野雅弘《昭和残侠传·血染的唐狮子》(1967年)
《日本电影110年》
四方田犬彦 著
牧野雅弘《昭和残侠传·请君归天》(1970)
讲座中四方田先生(右二)为大家放映日本电影片段。
四方田犬彦先生多年从事电影研究,他广阔的视野,使得许多散落在不同地方、被时光遮蔽的电影旧作重新被作为日本电影来审视,连同它所附着的历史信息,有些也与中韩相关。其实仅就他来京做的几场电影讲座,已经让不少观众认识到,亚洲电影之间,有着怎样密切的关联。尤其是辉煌时期的日本类型电影,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港台以及东南亚电影的制作。如同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港台歌曲,都曾是从日本歌曲翻唱。
电影节期间,四方田先生的这本书,一直被MOMA影城书店,摆在显著的位置。而他在这里所做的讲座与观众互动,集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日本的东映黑帮片与日活动作片上。如果没有他的提及,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港片《英雄本色》,是受日活动作片影响而拍出。同样未必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那个深沉、孤独的高仓健,并不是日本民众心中定格的高仓健银幕形象。
电影如果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认知,四方田先生觉得,那些大师精英们的电影固然值得看,但那些未必能走出国界,却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电影,同样值得观看。因为无名者的喜好,他们心中的历史,正是从这里面浮出来。
一 借鉴与改头换面,有一种电影叫日活电影
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被四方田先生界定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电影是大众娱乐产业的支柱产业。采取的是明星制,五大电影公司统治了日本电影市场,它们以每周生产两部的速度制作电影,所有电影院电影观众都坐得满满的。”“像我小时候去影院”,他突然做了一个掷毛衣的动作,看着毛衣稳稳地落在观众席前排一张空椅上,他解释说,当年他去影院,因为个头小,人又挤,每次都是中间休息时拿着外套赶紧跑到前面,一有空位就这样扔过去占座。
而那时候电影院多放的是日活电影与东映电影。“日活即日本活动写真公司,成立于1912年,和美国华纳、福克斯、米高梅是同一年。到今天已经107年。1945年日本战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美国占领之下。到1952年,日本虽然恢复了国家主权,但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还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电影领域也是这样。好莱坞的通俗剧、各种喜剧片、搞笑片、打斗片,诸种常见的类型电影都风靡日本电影市场。一个影响是,战前日本男星形象是脸要大,台词比较伤感,若再有些女性表情会更受人喜欢。而战后则变成,个头必须像美国人一样高,更加剽悍,且更具有硬汉气质。”
而日活的策略是,“从好莱坞引进一些素材,同时也向法国、意大利等国电影中借来一些情节,以日本电影的方式重新包装,请明星来演。也就是说,五十到六十年代之间日本对国际上的版权公约保护没有放在眼里。他们不在乎向海外借鉴并重新包装这个事实。”
以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怎么被日活电影拿来一用做例,四方田先生对比放映了它们中间相似的桥段,他同时指出,在同一时期的亚洲其他地方,日活的片子也被其他电影所模仿着。这是因为:“这些电影在许多地方广为上映——不论在香港、曼谷、台北,当时都有专门上映日本电影的电影院。许多日本电影导演也受邀到港、台导片子,无形间,日活的电影也影响到这些地方。”
“举个例子说,当时日活最著名的演员是石原裕次郎。而在台湾,也有一个本土的‘石原’,在当地电影中大显身手。他的名字叫黄秋田,长相都像。他后来也像《带吉他的候鸟》中的小林旭一样,扮演了一个类似角色。”
日本电影《带吉他的候鸟》1959年拍摄,而台湾1966年拍了电影《温泉乡的吉他》。将这两部电影的片段对比观看,在座的观众都看得无比会心。因为确如他所说:“里面的情节、主题歌、音乐都一样。”
“《带吉他的候鸟》讲的是什么呢?主人公带着吉他来到北海道,从坏人手中救出少女和她的牧场,为少女守住了牧场。但是他不可能停下来,他要坚持他的流浪天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太阳落山了,孤独的骑手骑着马,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夕阳和我,不知哪里有几分相像,我们总是一个人。我总是孤独一人。”
日本也有西部片的土壤吗?四方田先生解释说:“实际上在旷野上,夕阳西下,一个人骑着马远去,在日本是找不到这样的空间的。对于六十年代的电影观众来说,这是他们对西部的一种想象。因为这些片子外景地是在北海道拍的。他们把日本北海道都想象成日本的西部。我小时候就相信,在北海道,所有的人都骑在马上,随时快意地举枪射击。”
四方田先生还提示说,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韩国也拍了所谓韩国本土的西部片,但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东北。“也就是说,在当时韩国、中国(指大陆以外的地区,编者注)、日本也好,大家对美国西部片都有强烈好感,也都想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电影。”而这个源头,显然是来自日活电影。所以接下来的影响链就是:台湾、香港以及韩国,又把日活动作片搬过去,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改编……
四方田先生还记得,周润发在日本成名的时候,他去采访宍户锭——一位日活电影中的著名演员,据说拔枪速度非常快,也是四方田先生小时候的银幕偶像。他对四方田先生说,周润发手枪的打法还显得很幼稚。但他又很高兴,“四方田你看,三十年前我干的事儿没白干,后边有人追着呢。”
二 东映黑帮片,那时的高仓健何以受欢迎?
提到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影星高仓健,四方田先生一言以蔽之,“在日本人心中,高仓健可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即不是那个深沉、孤独、隐忍的形象。
“六十年代高仓健在银幕上塑造的完全是一些喋喋不休的、傻乎乎的形象。而直到1965年他出演的电影中,还是在北海道监狱里发起暴动的形象。直到七十年代,他出演的电影,只要他出手,未见刀起,对方已经毙命。”转型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但“多数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他,定格在这之前”。
而这样的高仓健形象,来源于东映黑帮片。
“东映的前身是战争时期的满映。大日本帝国崩溃后,当年的班底回国创立的电影公司。上世纪六十年代直到中期主要制作充斥着武士们打斗的古装片。后期开始拍摄以战前日本社会的流氓和赌徒为主的黑帮片。主人公虽然是流氓,但也在世俗的儒家的仁义之间摇摆。黑帮电影具有强烈反体制、无政府主义色彩,所以在六十年代末受到参加新左翼运动的学生们的热爱。”
黑帮片达到高潮是1970年。四方田先生介绍说,“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左翼运动骨干、学生看着高仓健主演的黑帮片,产生共鸣,并对他在片中的形象送出自己的掌声。1972年,日本左翼因为一个事件突然急剧冷却、消亡,随着这一变故,东映黑帮片也调整了路线,开始拍完全没有是非观的非常肮脏的黑帮片,尔虞我诈,无义之战系列。高仓健接受不了,就离开了东映,之后出演的都是《幸福的黄手绢》之类孤独中年男形象。”
而提到东映,四方田先生更有亲身体验,“我很小时候在东映电影里扮演了一个领路人角色,当时感觉东映公司片场,本身就像个黑社会现场。”
对比两大电影公司特点,四方田先生概括说,“日活,是时时刻刻把好莱坞欧美电影作为借鉴、搬演,连同制作方法一起拿来,去拍自己的动作片、人情片。它所塑造的银幕形象,都具有无国籍特点,也因此,这些故事、情节很容易被搬演到日本以外地区。”
而东映,则是常以战前日本为题材,故事中的流氓虽是黑社会形象,但具有鲜明反体制特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东映班底是从满映撤回来的,他们经历了伪满洲国的幻灭过程,虚构性,他们同样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也是有虚构性特点的。
日活是拍动作片的,但若拍起黑帮片,会是什么样?他们会把流氓拍成什么样?四方田先生的现场设问,吊足大家的胃口。之后他放映了铃木清顺导演的《刺青一代》片段,并提示大家关注里面的色彩与空间。“这部电影是把歌舞伎因素导入,色彩、节奏、空间感设置,都高度程式化。用了非常凝炼的手法和日本传统戏剧元素。”“如果说有和铃木清顺导演一同比较的导演,中国可能就是胡金铨。他曾经明确说,我的电影是把京剧用电影拍摄了出来。同样的话语,可以用到铃木清顺身上——他是把歌舞伎拍到了电影上。”
三 最终电影不是作品 而是能到达人们心中的历史
日本电影大师云集,做电影史研究的四方田先生却好像置大师于不顾,专门来讲这些电影,对此,四方田先生在提问环节做了回应。他说:“虽然大家对那些大师电影很熟悉,但日本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电影,是这些。而从这类有广阔群众基础的电影中,其实更能感受到日本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当有观众问询起日本当代作者电影状况时,他这样回应:“严格来说,电影不存在作者。为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电影是一个团队作业,有导演、制作、摄影,大家合力完成,在这个情况下,单提作者电影这个概念,不合适。但是有两个人在电影史上是个例外:卓别林和北野武。”
也有观众问道,当今的日本电影怎样才能在欧美电影市场上扩大影响,他这样回答:“与其说我关心这点,不如说我更关心、更希望它在中国会怎样……这个意思是说,与其希望文明差异非常大的国家,对方以异国情调角度关注,还不如希望它受到中国这样文化差异不那么大的地方人的关注。尽管中日社会形态有很大差异,但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底色,那就是儒家和道教思想。你把鲁迅的短篇、老舍的长篇拍成电影,拿到欧美电影节上不一定好。但是反过来说,我想像这样把普通中国人真正的喜怒哀乐细致描写出的作品,拿到日本放映,可能在日本会引起深刻共鸣。我个人认为,这种东西可以超越差异。”
让他觉得不满足的是,在日本能看到的中国电影,都是艺术性很强、导演主题非常明确的高雅的电影,以至于,日本观众都认为中国电影都是些高级高雅的电影。而当他身处这家电影院,看到的中国电影海报,却是各种类型的。“如果说到中国电影,当然我也关注陈凯歌的电影,但鬼怪电影、搞笑电影我也想看。陈凯歌的电影,是知识分子电影,我们能看出陈凯歌个人的所思所想。但看那些鬼怪电影,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无名老百姓的心思所在。”
他认为,在整个东亚的背景下,情节片、动作片、鬼怪片,都有一种共同的要素在作用人心。“为什么要在意欧美电影人对我们的评价呢?为什么不能在东亚之间去寻找能让我们共同感动的那样一种东西呢?”
四方田先生并不掩饰,他个人并不喜欢几位在欧美电影节屡获大奖的当代日本导演。“我能感觉他们已经能非常巧妙地迎合戛纳评委的口味。我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颓废的表现。”“如果我们只关注欧美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电影,我们不会了解本土电影很深的要素。一定有些要素是这样,它不会溢出这个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这之内,能让人产生共鸣。这些电影不是导演、作者电影,它是演员的电影,明星的电影。”
作为电影史家,他当然也注意到:“艺术的电影可以走向世界,被大家都看到,说这是日本电影,而本土电影往往只能在当代、在本土、特定的社会土壤中受到关注、欣赏。”但是,他还是坚持,“地方性的电影,描绘着在那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想象力、憧憬和希望。以那些为原型做成无聊的通俗剧,可能仅仅是恐怖或者是怪谈、奇人异事。看这些的时候,观众们的心理状态,会逐渐浮现出来。比如说,日本有120部的忠臣藏电影,今后应该也会不断出现。看它,会了解日本人的道德意识、悲伤的状态,并且明白很多事情。那不仅是武士的故事,也有艺人、武士的妻子的想法,里面包含很多东西。但这绝对不是艺术电影,忠臣藏并不能在国际范围内为人所知。只有日本人才看得懂忠臣藏。像这样的电影中国也有,是国内人都能看懂,而外国人却不懂。”四方田先生觉得研究电影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终电影不是作品,而是能够到达人们心中的历史。”
(特别感谢王众一、王小燕二位所做的翻译沟通,33、34版日本电影图片选自《日本电影110年》)
(原标题:日本电影史家来京讲日本电影
“日本观众心中的高仓健,和你们的不一样”)
来源:北京晚报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