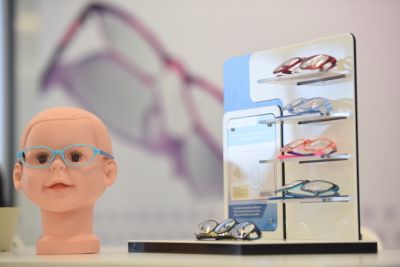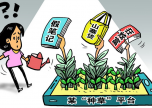暑假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假期。虽然天气炎热,但孩子们感受更多的还是欢乐。对于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北京人而言,他们的暑假生活也不尽相同。因此,回望不同年代北京小孩的暑期生活,人们也能从中窥探不同时代的印记。
作者:刘连良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物质并不丰盛,但当时的孩子们,依然能在大自然中感受别样的趣味,能从简单的生活中发掘属于自己的快乐。他们在胡同里捉知了,在田间地头逮蝈蝈,在干净清冽护城河里游泳……这份纯真和快乐,幻化成一幅幅场景,永存心间。如今,城市生活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与当年不一样。回首当年的暑期生活,不仅是再一次回味人生中最美好时光,还是对这座城市的年轮做一次梳理。
采访过程中,笔者和各位受访的同龄人都对当年中小学的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十分怀念与眷恋。那时的暑假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校外课堂和休整加油站。也是我们人生中值得铭记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金鱼池捞鱼虫回家喂鱼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在宣师二小(宣武师范附属第二小学)上三年级时的那个暑假。当年暑假的一天,母亲去人民大会堂开妇联表彰会,家里就剩二哥带着我玩。手巧的二哥做了个逮“蚂螂”(北京人管蜻蜓叫蚂螂)的网子。它就是用藤条做成网架、头上煨成个圆圈,再用小线编织成带兜兜的网袋,用它可以捕捉空中飞来飞去的“蚂螂”。
每年暑假,天气热、雨水多,往往一场雨过后蜻蜓满天飞。蜻蜓有扎堆的习惯,十几只、几十只一块从这头向那头飞行,然后再掉过头来飞,循环往复,并在行进中捕捉蚊蝇吃。胡同里的男孩们身着短裤、光着脊梁,忍着太阳的“炙烤”,聚精会神地盯着飞来飞去的“蚂螂”,看准时机,瞬间将手中的网子抄起又落下,“蚂螂”便被捉住了。
最有趣的是,二哥有一次一网子抄住了一对正在“驾排”(交配)的“老刚”(公)和“老籽”(母),它们是蜻蜓中体型最大的那一类,我们捏在手里都能感觉出它们的劲头。
那时,小孩子捉住蜻蜓玩是有“质量标准”的,虫体有伤的不要、爪子缺少的不要、翅膀折了或残了的不要,因此捉到手的成虫,我们格外保护。我和二哥这对“组合”在捕蜻蜓时,也是分工明确,二哥执网,我就负责把蜻蜓的翅膀捋顺了,夹在手指缝中,当我的两只手指缝里都夹满了蜻蜓才满意而归。
除了捉蜻蜓,我们还喜欢捉“唧鸟”(蝉、知了)。北京进入伏天后,“唧鸟”(蝉、知了)的鸣叫声越来越大。本地的“唧鸟”分大、小两个品种,大个的是“唧鸟”、小个的叫“伏天儿”,因其鸣叫声像“伏天、伏天的”而得名,而且更奇怪的是,一旦出了伏,小个的“伏天儿”还真就销声匿迹了。
暑假时,放了假的孩子们,把自行车内胎和松香熬成胶,粘在竹竿头上,然后钻进小树林去黏“唧鸟”。熟手儿一下午就能粘好几十只。知了粘回去之后,把他们关在一起,那震耳欲聋的“大合唱”让父母无可奈何。
三年级时的暑假,我家院子不算宽绰,只有有三间北房。母亲在东院墙弄了个花圃,种上了应时的花卉,我则靠南墙砌了个兔子窝养了只小白兔。后来,兔子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我带它到右安门外农产品商店结了个“临时婚”,不久它生了7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那真是人见人爱。与此同时,我还养了6只白羽毛的“莱杭鸡”(原产意大利,是产蛋量较高的一种),从雏鸡一直养到它们下蛋。当时,看到別人家养的鸽子成盘(?)的飞翔、蹲房,我也把鸡一只只抛上房去,让它们在那散步。当它们从房顶扑楞楞飞下来时,我也难掩心中的喜悦。
1963年的暑假,我和邻居小伙伴迷上了养鱼,既养金鱼也养热带鱼。那时候小孩没钱不舍得坐公共汽车,多远都是步行。我当时要从牛街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买金鱼苗,再步行到东单米市大街买热带鱼,当时买的鱼种有孔雀、燕儿、黑玛丽、红剑等。我养鱼的鱼缸也是自己动手做的,用角铁、水泥与玻璃粘合而成。喂鱼的食料则是自已捞回来的鱼虫,那时候,出了右安门往南就是草桥,那里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园子,小河和灌溉渠里有鱼虫,我和小伙伴拎着纱布抄子在这里捞够了鱼虫才会回家。
对于捞鱼虫,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天坛附近的金鱼池,那时的金鱼池还是公园里的一大片水域。它的湖中有一种体型较大的鱼虫,叫“苍虫”,当时很多人穿着游泳裤,下到湖里去捞“苍虫”,最多时,在宽广的水面上有近百人同时在捞鱼虫,当时的场面可够震撼的。现如今,金鱼池一带,楼房林立,焕然一新,又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里当年垂柳依依、碧波荡漾的风貌呢?
成天腻在少年之家

63岁的田雨,是市公交集团的退休员工。她的小学时代是在西城区武定侯小学度过的。据田雨回忆,当年学校放暑假时,老师会根据学生住家的远近,安排暑假学习小组。每个组3至4人,在谁家谁就是组长。那时,同学们每天早上去学习小组做暑假作业,做完作业后可以到学校里的暑期少年之家玩。少年之家也是为双职工家长无暇管孩子而设。田雨说,那时少年之家全天开放,她和同学们没地方去,就成天“长”在少年之家。少年之家里有图书室,还有唱歌、跳舞、朗诵和手工等兴趣班,这些班都是免费授课。而且,暑假的时候,操场上清静了许多,单杠、双杠随便玩,荡秋千也甭排队,上去后就在秋千上悠来荡去,特别过瘾。
田雨暑假里要是赶上姐姐休息,她就准缠着姐姐带她去看电影。她小的时候最爱看《画中人》、《飞刀华》和外国的《忠诚》等影片,并且从中获益不小。
田雨小时候时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爱好,那就是爱看母亲做棉活儿。在她印象中,母亲做棉活儿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每年气温上来以后,那时全家人脱下的棉袄、棉裤已经拆洗干净,此时找个空闲时间就做一件。田雨瞧着母亲先把棉衣的里、面用水喷湿,再用烧热的烙铁熨平,然后再往棉衣里子絮棉花,并且要新旧搭配,这样冬天穿起来才能既暖和又柔软,还节省开支。絮好了棉花,再把面布铺在棉花上,就可以“行”(用针线将里、面和棉花固定为一体)了。田雨还观察到母亲为了“行”直,先用针在布上划出线,再沿着线一针一针地“行”。衣服基本成型后,母亲会撩边儿、上领子、钉扣子这样一件棉衣这才完成。儿时的田雨看着母亲辛辛苦苦地做活,将他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母亲这种少说多做的品格也深深影响了她。后来田雨结婚成家,她也继承了母亲吃苦耐劳的风格。田雨说,“我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如今,老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也更加理解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深刻含义。”
走进农村长见识

今年62岁的美茹,退休前是市机械局下属某厂的工会干部。美茹少时就读于东城区泡子河小学。给美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年级那个暑假,当时她的家就住在北京站旁边,她们班有个同学的妈妈又恰好是20路公交车的售票员。暑假里,美茹和小伙伴一起“学雷锋”,来到汽车总站帮助车站工作人员打扫卫生,给高温中开公交车的叔叔、阿姨送盐汽水防暑降温。她还登上公交车为乘客背诵《毛主席诗词》,稚嫩的童音、朗朗诗韵让南来北往的客人赞不绝口。后来,美茹的“宣传队”还步行来到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下乡锻炼,为村民表演歌舞、快板等节目,并一起下田参加劳动。当年美茹她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到了乡下两眼一抹黑,真是五谷不分。暑假到农村锻炼,可算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提及下乡锻炼,我的体会同样颇深。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并不富裕,暑假时,还要跟着母亲做一些外活。我曾做过临时送奶员,也做过装订书籍的工作,还为厂甸加工过糖葫芦签等。有一年,我们利用假期到我大哥所在的西山农场小住,在那吃到了从没见过的大白贡杏和正宗的京白梨。我头一次看见黑白花大奶牛竟然吃着当时紧俏的胡萝卜、白薯和带鱼段,这令我“羡慕不已”。原来这些奶牛每天要提供大量牛奶,饲养员必须按食谱提供饮食补充。如今,我大哥已经归真,想到此谨以此文作为怀念。
现供职于某科技公司的段芳女士,小学六年是在原崇文区打磨厂小学度过的。段芳学习成绩优异,多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她的印象中,每到放暑假时,作为家里的长女,帮助上班的家长照看好两个妹妹才是暑假的“主旋律”。不过,1983年的暑假,让段芳印象最深:那年她参加了原崇文区的三好学生夏令营活动。这是她头一回走出北京城,走进门头沟的大山深处。她得以参观潭柘寺,了解其悠久的历史,潭柘寺里两棵蔽日遮天的帝王树和配王树,令她深感震撼,而正是在那时,她深深体会到潭柘寺的幽静和历史的悠久,也才相信“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绝非戏言。
至今,段芳还真切地记得,那个小山村的饭菜味道好极了,特别是那新鲜的煮玉米香甜可口,令人难以忘怀。唯一的遗憾就是当时庙里的和尚都不知去哪了,没听到诵经之音和晨钟暮鼓。那个暑假让段芳引为骄傲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年中南海有限开放,作为三好学生的段芳有幸得到了中南海的参观券,走进了菊花书屋和西花厅领略了伟人的风采。这在当时可是少有的殊荣。
女孩把逮蛐蛐写进文章
当年的暑假,孩子们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游泳。那会儿,孩子没钱去不起陶然亭游泳池,就只好去护城河游泳。如今,护城河里一到热天,也是围满了游泳的人,虽然岸上有“禁止游泳”横幅,但仍然屡禁不止。当年,我们孩子们游泳时都是几个人结伴而行,一则互相照应,二则还可以壮胆。那时候的护城河水质非常好,清彻见底再加上夏季是丰水期,确实是游泳的好地方。我记得宣武门西北角的护城河上有一座废弃的铁道桥,桥下河水水深面宽,是孩子们练跳水的理想之地。一个个晒的跟黑泥鳅似的男孩争先恐后地象下饺子样的扑通、扑通往水里跳,形成了夏日里的一道风景,令人多年后不忘。
1964年暑假,我的小学生涯结束了。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时,我便是北京六十六中一名中学生了。
进了重点校,同学们都是“尖子生”,我这才感觉到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开学不久的一次语文摸底测验后的作文点评课上,语文老师就读了一位同学习作,到今天我还记得它的梗概,文章就是讲暑假里捉蛐蛐的事儿。不过令人惊喜的是,这篇文章将捉蛐蛐的过程写得非常详细。比如,有“昏暗的路灯下,寂静的小巷中这蛐蛐儿的叫声仿佛就近在咫尺,可又只闻其声不现其身。我象个侦察兵打开手电筒,拎着探针和蛐蛐罩子蹑手蹑脚追寻着声源”等字句。老师读完之后,做了点评。老师又让同学们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人说了张三、也有说是李四或王五,老师答曰都不对。大家伙面面相觑之时,老师说出她的名字:王慧!大家都惊呆了。王慧是一个文静少语的女孩,大家都纳闷:她写逮蛐蛐儿的事怎么比男孩还棒呀?何老师也表扬王慧善于观察生活,写文章时勤于思考又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此时教室里掌声骤起。
说起逮蛐蛐儿,那应该是北京男孩子们的专长。我记得四年级的暑假,一天下午我和小伙伴拿着“装备”,出了广安门就奔菜户营去了。那里广阔无垠的庄稼地是蛐蛐儿们的大本营。水渠边、机井旁、豆秧子下、田埂上都是蛐蛐儿喜欢做窝的地。小伙伴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前进,地面上有两个障碍物让人无法忍受,一个是剌剌秧,一个是蒺藜狗子,这两样碰上谁都剌的人够呛。有一次我为挖出蛐蛐儿窝的洞口,不小心碰触到杂草上面的马蜂窝,呜拉一下子,群蜂乱螫顷刻之间,把我身上螫的到处是大包,为躲避马蜂的进一步攻击,我摔了一溜跟头才脱身。
跟着宣传队参加汇演
曾在某大型国企任压力容器电焊工,今年54岁的俞振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朝阳区大郊亭小学的学生。在那个讲究学工、学农、学军的办学时代,孩子们就盼着每年夏天的期末考试因为这就离放假不远了。俞振国说,期末考试以后,班主任老师会按照各个学生住家的远近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俞振国家住北京啤酒厂家属宿舍,他所在的南院里有住户42家,和他一般大的孩子有六个,这六个孩子就顺理成章地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那时候做暑假作业前要先抄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不过,做作业时,大家并不认真,都是互相抄,以致于大伙的学习成绩也是马马虎虎。最令同学们高兴的是作业后玩过家家的游戏。
俞振国说他喜欢扮装成“爸爸”,因为他爹是厂子里的司机,所以他也装成开车的“爸爸”。其使用的道具“小孩”,是女同学拿来的布娃娃,他们玩得乐此不彼。有时候,在暑假,他自己经常溜进啤酒厂和酿酒车间,潜心观察车间那庞大的啤酒罐、不锈钢管道等设备,他对这些设备很感兴趣。这个爱好促使他高中毕业后来到企业里当了一名电焊工,经过多年苦心钻研,他也拿下了国颁二级压力容器操作证,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
今年63岁的李伦是东城区房地中心的退休干部,也是本市小有名气的业余男低音歌唱演员。在其加盟的广播之友合唱团担任主唱,并且出访过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李伦提起少年时的暑假生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后来的工作及业余爱好都跟上小学时五彩缤纷的假期生活密切相关。当年,李伦喜欢唱歌,但因念小学时,岁数小,就没有按受正规的声乐辅导,只是凭着喜好和自身的模仿能力跟着别人哼唱。那时,小小少年李伦因为喜欢评剧名家马泰先生的唱段,进而喜欢上了评剧,通过自学,很小的时候就能唱《小二黑结婚》、《夺印》和《杨三姐告状》等唱段。
有一年暑假的一天傍晚,李伦跟着宣传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汇演。当乐器响起时,观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是李伦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唱戏,他当时心里像揣着只小兔子嘭嘭乱蹦,两腿不由自主地哆嗦。可是当锣鼓点响起时,李伦就忘了周围这些,迅速入了戏,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唱开了。他那天唱的是评剧《秦香莲》选段:“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在一堂。父子义、夫妻情你怎能忘。欺君罪由我包拯一面承当。劝驸马你还要再想再思,再思再想。难道说你是铁打的心肠……”
一曲慷慨激昂的包公唱段,博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李伦唱完后也是特别兴奋,鞠完了躬,昂首挺胸走下了台。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