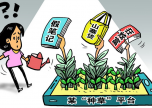北平解放前后的记忆:女教员打毛衣挣外快 被宋庆龄邀请看话剧
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但是平民的生活依然困苦,我家应属“殷实”之列,可有时还是两手空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张京生、王元珍合作 1979年
我家住在上堂子胡同18号,1946年9月我上学了,学校在家的斜对面,叫上堂子胡同小学,由三个院落组成。
小学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入学时要自带桌椅,父亲托人打造了一套新桌椅随我入学,可没过多久,新桌椅就融入到众多破旧桌椅之中,不见了踪迹。一天,前院的教员休息室外排起长队,大家都来领取“美国援华物资”,我领取了三件物品:一大包用报纸包裹的奶粉,一件很好看的白色儿童连衣裙,一件纯毛的西式男裤。奶粉家人不喝,只好由父亲受用;白色儿童连衣裙,妹妹穿了三四年;姐姐大我七岁,心灵手巧,把西式男裤改成女裤,也穿了许多年。学校后院操场的西北角有一破旧低矮的小屋,居住者是年迈的关老师,他孤身一人,原本有个女儿但因贫困送给了别家。关老师上课的形式有点像给学生们讲故事,如今回忆起来,他酷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与学生的关系很好。而学校的女教员们在课下打毛衣挣些外快,据说临近解放时,已开不出工资。
临近1949年,市民的日子不好过,以至于到了恐慌的地步,市面物价飞涨,纸币越来越不值钱,大家都认为银元如“袁大头”与食物同等重要。东花市与小市口的交叉地带,经常有人倒卖银元,他们手中捏着两三个大洋,口中念念有词,“买两卖两”……不远处的胡同里还有人用银元进行赌博:在地上划一横线,从一定距离把银元投向横线,压中横线者为赢家。我家条件还算可以,母亲敦促父亲买些面粉存起来,记得家中还买了不少豆饼,做了点黄酱已备不时之需。至于穷苦之人,无路可走。
围城后,市民的日子更加紧张,大家偷偷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消息,市面上也出现了光怪的现象。不景气的商家用“话匣子”播放着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服裤子短大衣,旁边坐着个“大肚皮”……一些报纸说有位“杨妹”能许多天不进食而生存,并且每日跟进报道现状;市区内的散兵游勇多了起来,最可怕的是那些伤兵,为防万一,我家在睡觉的炕上挖了一个暗洞藏身,内置一木箱,把母亲的大衣父亲的皮袄藏在里面。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记忆中,我第一次看见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是在花市大街与羊市口的交叉处,厚实的浅黄绿色棉军装,军帽上的羊毛很长,军帽下是一个个又红又黑的面庞。不久后,军管会工作组进驻小学,并在操场上举行见面会。平时校长在操场“训话”时,一定要站在用砖垒砌的高台之上,可是这次工作组的领导没有上台。我的个子不高,站队靠前,因此得见他的样貌。他是位个子很矮的小老头,脸庞白中透红,眉毛颜色很淡,四周皱纹偏多,穿的军装没有特殊之处,布鞋上有明显的黄土痕迹。他操着一口西北口音,讲的内容多已忘记,只有开头那句话我至今难忘:“我们是先生,你们是后生。”我听后觉得很新奇,不叫“学生”叫“后生”,这一定是农村对小孩的称呼。多年过去,如今再琢磨此事,一个先生,一个后生,只是生的早与晚罢了,都是“人生”。从那之后,老师训人的口气少了,再也没有用戒尺打人的举动。
“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这样的流行歌曲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旧社会好比黑咕隆冬的枯井万丈深……”“高楼万丈平地起……”等耳目一新的歌曲。学校内也一扫过去的沉闷气氛,有了新的生机。记得学校排演了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家住在花市大街的一位高年级男生出演哥哥一角,每次演出都真的吃窝头,喝凉水。同学们从花市大街路南的山货店买来细竹竿,两头削出“方槽”,从家中找铜钱儿和各色布条,安于其上,成为集体打霸王鞭的用具。有一天,上堂子胡同来了一个短发的军管会女兵,她教我们这群小孩唱歌。以此经历,在三十年后的1979年,我创作了油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还参加了第五届全国美术大展,并获得银奖。
此时期的一天,家里还真来了一个解放军,在他身旁还有个小解放军陪同。大人们寒暄过后,我才得知他是我的老舅周克文,抗战时期在老家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现安新县)从军。我母亲从十四岁时就照顾老舅,直至出嫁后才分开,两人的关系远超一般姐弟之情。一日,老舅邀我们去前门附近的大众戏院观看京剧《三打祝家庄》,戏院门口人员众多,但多是军人。演出很精彩,情节曲折、布景华丽,台上的帐篷和串串红灯笼非常好看(京剧演出很少用实物做布景)。多年后才得知那是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主演的“延安评剧院”版本,据说毛主席当年还曾评论过。那时老舅周克文担任肃宁以及泊头的领导工作,后来一直在河北工作直至退休,2018年9月离世,享年九十五岁。
1949年底,我家搬到崇文门外大街附近的南五老胡同21号,院中有个空屋子,曾有几位解放军暂住过一段时间,我与房东的孩子彭延年相处得很好(我称彭延年为“九哥”,后来他成了我的姐夫)。北京的时局尚不稳定,我记得那时胡同中的路灯非常昏暗,但晚上卖豆腐脑小贩的电石气灯很明亮,就在这时,解放军战士进行巷战演习,端着枪的战士从远处快跑过来,停在我家大门口,气喘嘘嘘地做着警戒动作……当时我已转学至北京汇文第一小学,上学路上必经正阳门连接的城墙附近,我亲眼见到在城墙上驻扎的防空部队架设了许多门高射炮。三十年之后的1982年,我又创作了油画《家乡喜讯》(现藏于天津市文化艺术联合会),此画还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术大展”。
初入上堂子胡同小学学习时,我还不满六周岁,校址酷似一座大庙,有些阴森,加之我的年龄太小,老师的教育方式又古板严厉,故而我的小学学业是在压抑和恐惧当中度过的。当时我还体弱多病,性格内向懦弱,在校最后一个学期的总成绩为全班“丁等第四名”。那会儿学习成绩先以“甲乙丙丁”四级划分,丁级属于不及格,还排在第四名,成绩之差可想而知。上学时我还挨过戒尺的打,手心又红又肿又烫,人的尊严与自信,对我来说等于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转到北京汇文第一小学学习,一是时代变化了,二是我在新学校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孙敬修先生。众所周知,孙敬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当时孙先生除了任教导主任之外,还兼任美术科教员。在他的教育和关怀之下,我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1年,我戴上了红领巾,参加了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很快我又成为班上的美术骨干,教室墙报上所有的装饰及画作都出自我手。我画的克里姆林宫和天安门的形象十分逼真,志愿军的英姿以及“大鼻子”的麦克阿瑟也曾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已至班上“中等偏上”的位置。后来,孙敬修先生推荐我和其他两名小朋友到西单六部口附近的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广播剧播出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太像我,很新奇。大概是1951年,我和众多小朋友被宋庆龄奶奶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话剧《我们都有一个志愿》,那闪闪发亮的金黄色天鹅绒舞台口大幕至今印象很深。回校后不久,我们自排了同一剧目,我有幸参与其中,并在学校大礼堂演出。
临近毕业,孙敬修先生送给我一张他的相片,并在广播电台送给我的红紫色绒面日记本中写下“京生是位好学生,将来定有作为”的勉励之词。从“丁等第四名”到如今的“好学生”,是孙敬修先生让我有了人的尊严与自信,成就了我新的人生起点。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止一次地做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北京不解放,我会是什么样子?乐观想,可能继承父业,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悲观想,我这个“丁等第四名”很可能成为败家子,总之拥有大学教授的身份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至今,我一直深深地感谢我的恩师孙敬修先生,感谢时代的变迁,感恩时代的进步。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京生
流程编辑:tf011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