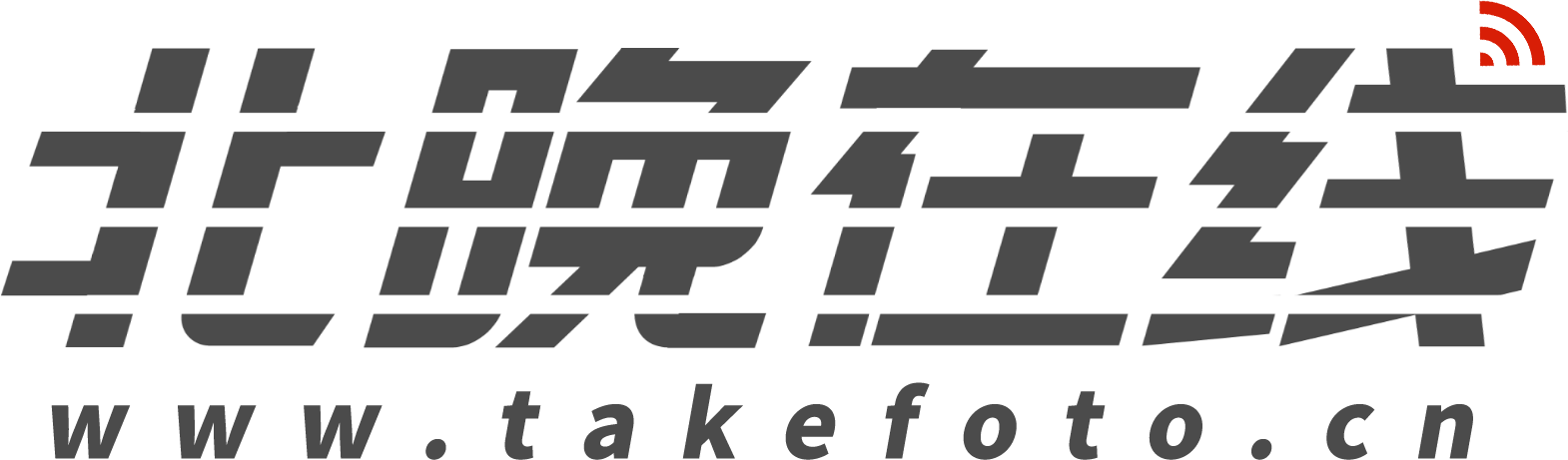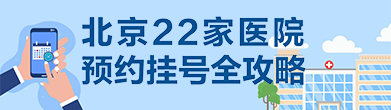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

回家路上,我们在想些什么
为期九天的“超长”春节假期将至。从北国雪野到江南水乡,从城市通衢到乡间阡陌,数亿中国人如同归巢的候鸟,在岁末年初的时节踏上“迁徙”之路,朝着名为“故乡”的坐标奔赴。 每...
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 -

AI时代,老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2026年初崇礼论坛上,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针对AI时代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升级,中国中小学教师一大半是不合格的?”“若AI能更高效精准传递...
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

会交流、能干活的机器人是怎样“练”成的?
新华网北京2月17日电 打醉拳、演小品、能取货……马年春晚舞台上,不同类型的机器人组团登场,上演了一场科技版万马奔腾,成为新春最具未来感的风景线。 图为2026年春节联...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