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90后青年学人罗雅琳:乡土的新美学,并非回到田园牧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乡土的叙述是一方沃土,因此,吴晓东教授在为青年学人罗雅琳的新著《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撰写序言时,有几分“担心”地提到:在这一学术领域,想获得新的研究角度、视野和方法似乎已不那么容易了。
作者:曾子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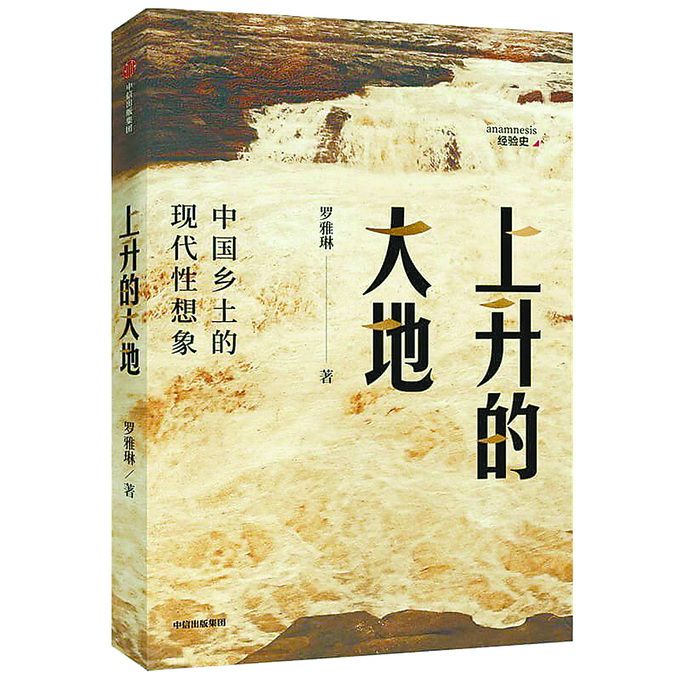
《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
罗雅琳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正因为关于乡土的前人研究十分丰富,所以它们构成了我在读书阶段需要一直学习和对话的对象。”时间回溯到2013年,最初触动罗雅琳零碎想法的,是于这年出版的两本书: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修订本)》和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这两本书帮助我破解了那种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使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理解一些常见的文艺作品。我不敢说自己‘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只能说,写作总是与想要创新的冲动相关。”
还有三位学者构成了《上升的大地》一书的“知识原点”:李欧梵、费孝通和刘小枫。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是罗雅琳这一代学生在学习现代性理论时的必读书目,它讨论了在西方都市文明影响下,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上升的大地》将目光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了中国内陆地区,试图挖掘出西部中国“别样”的现代性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则是讨论乡土问题时绕不开的经典著作,在罗雅琳看来,其中的很多概念在后来的沿用中逐渐变得刻板化。刘小枫对《上升的土地》的影响则是十分微妙的,罗雅琳只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提到,自己是在阅读他关于80年代的同道友人萌萌的纪念文章时,发现“土地”这个词极其频繁地出现——“我想,这种‘土地感觉’,或许构成了理解以往被视为在欧风美雨浸润中诞生的80年代文化的另一条线索。”
“上升的大地”是罗雅琳在中国乡土遭遇现代性的诸种经验中提取出的一个意象,她始终关注那些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最令人振奋的形象:在广阔的西部内陆地区,真正“愉快”的人民;《黄河大合唱》中充满力量、遍及天下的黄河;不受主流文学待见的《平凡的世界》里,蕴含着的一种农村人对现代性的世纪向往。
在“学术气”不那么浓的一章中,通过对“离乡-进城”的几种代表性叙事的考察,罗雅琳继续论述了何为“想象的乡愁”——那些以“落后的”形象出现在“乡愁”文学中的乡村,仍旧被预设在了与城市对立的位置。《上升的大地》最后落脚于科幻作品,罗雅琳发现,在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幻想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不是象征着现代力量的海洋,也不是“天空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火”与“气”,而是“大地”和有着“大地性”的中国形象。当一代年轻科幻读者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时,那些“落地”的幻想则提醒我们,土地性的经验依然继续为未来世界的人类提供着精神养料。
中国传统的乡土主题就这样飞升到了想象力的世界。跳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既定框架,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建构一种新的整体性,成为了《上升的大地》的核心论述脉络,同时,也描摹出了属于未来的乡土视野。
罗雅琳:我希望勾勒出一条不同的乡土美学线索
书乡:《上升的大地》所在的系列被称作是“经验史”的写作,什么是“经验史”的研究方式?
罗雅琳:“经验史”是这套书系的总策划人舒可文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她没有给我们很严格的限制,我也是在跟集体的讨论和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逐渐把握到它的一些内涵。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经验史”有四个层面。第一,一般来说,“经验”总被认为是个体的、私人的、碎片化的、反宏大叙述的东西,总是存在一个“小经验”和“大历史”之间的对抗结构,比如常见的“一个人的历史”的说法。这背后其实预设了一个完全自在的、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体。这种个人主体当然只是一种想象。这种以“小经验”解构“大历史”的做法,是“经验史”首先要反对的。第二,我想引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说的“情感结构”或“感觉结构”来帮助说明“经验史”。雷蒙·威廉斯的研究总是从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抵达对于社会总体状况的把握。文学艺术作品看起来是艺术家个人的自由创作,体现的是个体的情感活动,但雷蒙·威廉斯指出,这种情感方式其实受到了整个社会总体性和支配性的情感结构的影响。而这个整体的情感结构,是由社会的组成方式、经济生活的运行方式等所决定的。所以,情感经验不是完全私人的东西,而是可以勾连起非常社会化的层面。“经验史”对于经验的理解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式。第三,“经验史”强调经验的历史向度。也就是说,经验不仅是被当下的社会所塑造的,也是被历史所塑造的。所以这套书系中的书目都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第四,“经验史”强调要讨论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要注意反思西方理论框架的限度。
书乡:您自身的“乡土经验”来自于何处?为什么这些间接的、审美的经验和体验,能够为没有直接乡土经验的研究者提供支撑?
罗雅琳:我小时候有过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我的母亲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更重要的是,我成长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城乡结合部。在我就读的小学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孩子几乎各占一半。读中学时,我每天上学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泥巴路,要穿过菜地、溪水和猪圈,另一条路是宽阔的大马路,路边有大超市和银行。这是非常典型的“城乡交叉地带”的景观,我甚至多次看到猪在大马路上走。当然,更多的“乡土经验”还是来自电影和阅读。文艺作品往往是时代意象的提炼,也最能使某种关于乡村的理念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所以这本书是以对于电影《山河故人》中两种空间里的两种颜色的分析作为开头的。书中所说的“乡土经验”,更侧重于乡土在进入文化表达之后所发生的形象变异。它不(完全)是乡土生活的经验,而是大众对于乡土的感知经验。也许会有人认为,大众通过种种文艺作品所感知到的乡土与“真实经验”存在距离,其间发生了种种审美的、政治的变形。但这种变形的过程也是一种真实,是值得去思考的“经验”。
书乡:提到“现代性”,我们通常都会承认它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的事实,要怎么理解中国的农村的“别样”的现代性?
罗雅琳:所谓“乡土的现代性”,换个说法其实是“革命的现代性”。因为无论是“长征”之后的中国革命,还是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在以乡土为腹地的国家形态中成长起来的。它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现代性样态,所以,我要强调“土”不等于“非现代”。

电影《山河故人》里,乡土的色调是沉重、灰暗的。
书乡:“现代性”一定是进步的吗?“上升的土地”把“现代性”与“上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又要怎么面对现代性中蕴含的悖论?
罗雅琳:“现代性”当然不一定是进步的,现代性的进程中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考虑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以那种颓废、破败、前现代的形态来呈现乡土的文艺作品太多,所以,我希望勾勒出一条不同的乡土美学线索,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讲出在落后的经济环境中依然具有饱满精神状态的人,这是“上升的大地”之“上升”的含义。另一方面,我认为现代性的悖论只能用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关于农村问题的常见忧心,诸如农村的空心化、农业劳动的辛苦,都只能通过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来解决。我们不可能退回到桃花源式的原始生活中去。
书乡:在书中你提到了路遥的作品为大地上的农民思考了一条“上升”的道路,却始终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可。始终得不到认可的原因是什么?路遥的作品有别于那些幻想平民子弟“飞升”的“YY作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
罗雅琳:路遥和刘慈欣一样,他们采取的写作方式和美学理念都有别于80年代“纯文学”体制所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难以被安放到“主流文学”中的恰当位置。但他们所吸引的广大读者——一个有别于80年代“纯文学”所召唤的读者的庞大群体,却推动着他们进入一种可以说绝对主流的位置,获得官方的认可、奖项和职位。路遥的作品有别于白日梦小说之处,我认为在于他不仅关注农村青年如何获得物质和事业层面的成功,更关注他们如何获得精神层面的高贵。他在《平凡的世界》里不仅写了通过办砖厂致富的孙少安、考上大学的孙兰香,还写了事业并不成功的孙少平,并且反而是孙少平最为打动人心。通过孙少平,路遥希望表达一种激励:虽然奋斗的结果有可能失败,但人们仍可以获得精神上的高贵,或者说,奋斗精神本身已经赋予人以一种高贵性。
书乡:书里提到,校园论坛里讨论的现实话题和老家烦人亲戚的问题如出一辙、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生活需要掏空遥远的“六个钱包”……这些零碎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是不是都直接来源于您的真实感受?
罗雅琳:对,这些都是我的真实感受,这是一种生活体验与文艺经验的互相印证。我读中学时,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英语听力基本上都是用录音机和磁带播放。2009年我从湘乡去南京上大学时,为了方便学英语,特意新买了一个放磁带的复读机,结果去了南京之后,发现英语书配送的都是光盘,已经没有人用磁带了,也根本买不到磁带。这个复读机也就一直保持全新在柜子里躺了四年。所以,当我后来读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发表在杂志上时反响平平、通过广播播送却引发巨大影响时,一下子就明白了:不同的媒体的背后是读者群体的差异。
书乡:您也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警醒:自己秉持的会不会也是一种“飞岛上的视角”?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警醒?由于经验是不会断裂的,在近期的生活中,对于中国乡土,您有没有获得什么新的经验?
罗雅琳:需要这种警醒,是因为我可能在反对某些关于乡土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了另一种想象中的乡土。最近的经验与李子柒有关,我很喜欢看她的视频。很多人批评她对真实的乡村进行了过度的美化,但我觉得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把李子柒的视频当做一种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乡村纪录片来看,很多东西就可以得到理解。让城市里的观众感到心灵的慰藉的,不是真实的乡村生活,而是李子柒所展现的那样一种和谐、自由的劳动状态和生活可能性。但这种自由状态只能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在农村,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像李子柒那样生活。农业劳动的辛苦最终还是要靠现代技术、现代工业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感受到了路遥的特别之处。《平凡的世界》里展现了80年代农村出现的全新经济要素:乡镇企业、包产到户和农民工等等,孙少平和孙少安是在这个全新经济要素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新人。当下的中国如果要展现一种关于乡土的新美学,我想,一种可能的方式不是回到传统的田园牧歌里去,而是要呈现新的生产力状况下所诞生的新人。
(原标题:90后青年学人对中国乡土的飞升想象 乡土的新美学 并非回到田园牧歌 )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0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