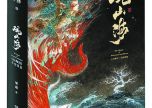2016年3月14日讯,1924年11月,已经退位的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和他一起出宫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十名宫女、太监和随从,这其中有一名70多岁的老人。他一路走一路回望高高的宫墙,目光悲凉,这是他呆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他不知道离开了皇宫,自己的一身技艺还有何用。这位老人就是清朝最后一代宫廷画师李挺梁。后来他无数次和孩子们说起这锥心刺骨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传承了数百年独树一帜的宫廷画技艺就此沦落民间了。

王竹坪临摹郎世宁八骏图
80多年后,我有幸从李挺梁后人的口中,听到了最后一代宫廷画师的故事。清末国运衰微,郎世宁那一代画师的辉煌早已经成为过往,他们在紫禁城中几十年如一日用画笔营造出盛世景象,直到走出宫门的那一天,才知道世界早就变了模样。
宫廷画师消失了,幸运的是,宫廷画技艺经历时代变迁,险遭没顶之灾,最终流传了下来。
最后的宫廷画师李挺梁和他的传人
在幽静的莲石湖边,王伟有一间小小的画室,画室的墙上贴满了宣纸,上面是怒放的牡丹。他在这里潜心作画,正在准备个人画展。
王伟是宫廷绘画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宫廷画师李挺梁是他的姑老祖,也就是爷爷的姑父。“我爷爷王竹坪从小跟着姑父学画,做他的书童,每天和他一起进宫伺候,所以尽得姑父的真传。爷爷把这个技艺传给了我的叔叔和姑姑,我是从小跟着爷爷学的,如今我的孩子也在学,已经传到第五代,宫廷画技艺会一直在我们这个家族传承下去。”
关于这位姑老祖李挺梁的故事,王伟都是从爷爷口中听来的,可惜的是并没有照片或者画像留下来,他甚至不知这位前辈长什么样,关于他的史料也很少,他的一生浓缩成《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中的两行字:“李挺梁,字云轩,清代画家,京师人,擅长指头画。”
指头画据说是李挺梁的独门绝技,用手指蘸上墨水颜料作画,这并非宫廷画技法,应是他闲暇时自娱自乐的玩意儿。王伟保留的李庭梁仅存于世的一张画就是指头画,很小的一幅,画在一个类似钱夹的袋子上,百年旧物,带着斑斑污渍和岁月的痕迹。
“听爷爷说这个东西是放奏折用的,有时候姑老祖向皇上汇报事情,就把写好的折子放在这里面带进宫去。”这是一幅画得很随意的静物,题写着“事事平安富贵吉祥”,是老百姓最普遍的愿望,落款为“砚华史李芸轩偶作”。
“砚华史是他当时的官职,为五品官。听爷爷说,这位姑老祖少年便才艺超群,1873年丁丑科进士入宫,才21岁就成为宫廷画师,一度掌管如意馆,历经咸、同、光、宣四朝,在宫里服务皇家51年。有一段时间他颇得慈禧太后赏识,在颐和园住了不短的时间。”1970年,王伟曾在颐和园佛香阁楼梯西侧转弯的平台上发现一幅《花卉五福图》落款正是李芸轩的名字,应为姑老祖的作品,在乾清宫内室的东墙上王伟也曾见过他的作品。

末代宫廷画师李挺梁仅存于世的作品:指头画,即用手指头画的画。
宫廷师独特的传统
宫廷画作为一个独特的画派在中国已经出现近千年。相传五代时期黄筌供奉西蜀的翰林图画院,为御苑中的奇花珍禽、名木怪石作写生,作品富丽堂皇,反映了宫廷的审美趣味,被称为“黄家富贵”,为宫廷花鸟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徽宗画院的花鸟画达到极盛。他为了提高书画的地位,破天荒的把书画列入国家科举制,定期出题取仕,从全国招收优秀学生。
在康熙年间,宫廷绘画呈勃兴之势,至乾隆朝达到鼎盛。内廷设有专门管理宫廷画家的机构,如康熙时的“造办处”,雍正时的“画作”,乾隆时的“如意馆”、“画院处”。
李庭梁在宫中供职的地方便是“如意馆”,属于皇室的服务性机构。此处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绘画大师,书法家,瓷器大师,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据王伟的爷爷王竹坪回忆,当年宫廷画师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给皇帝、皇后、太后等皇室成员画肖像,李挺梁先后为慈禧太后、载淳(穆宗)、载恬(德宗)、溥仪画过像。
王竹坪10岁拜姑父为师,被收为义子,作为书童常跟随师父进出宫禁,对如意馆的情况也略知一二。据他说,宫廷用的画纸极为讲究,平时作画用的有冰雪宣、蝉衣宣、夹江宣、煮捶宣、贡宣、云母宣等等,但是给皇上画像用的是一种纯金打造的极薄的金箔。墨也是特制的,研磨之后会散发浓香,含有名贵的药材。李挺梁曾经拿回家一块带云龙纹的墨,家中小孩鼻子出血,研一点磨喝下马上就好,竟成了一个偏方。
宫廷画师有一个传统,就是对颜料极为考究,通常会自己制作,用的是纯天然的植物和矿物。然而,谁也想不到竟为一桩家庭悲剧埋下伏笔。中国画颜料的藤黄有毒,王伟的爷爷王竹坪在家中制作颜料,大女儿误食了藤黄中毒身亡,令全家悲痛不已。

王伟在作画
离宫前画师们用相机拍下故宫名画
在王伟的手中,还珍藏着一件李挺梁的遗物,是一个硬皮的册子,上面写着《名画集锦 云轩珍藏》,“这其实是宫廷画师们自己制作的一个日历,当年宫中有洋人进贡的照相机,如意馆的画师也有机会偶尔使用,溥仪退位以后,姑老祖大约也感觉在皇宫的时日无多,便和几位画师一起用相机把故宫珍藏的一些名画拍摄下来,拍了几百幅。出宫以后,他们把这些照片影印下来,选了360幅,做了这样一个日历。”
这是一个真正的“限量版”日历,一共只印了8件,几位宫廷画师各自珍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劫难后,如今这些名画真品有的不知所踪,有的流失海外,他们的影像在这本发黄挂历中,依然是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
命运坎坷的不仅仅是这些名画,还有画师们和宫廷画的技艺。1924年,最后的几位宫廷画师随溥仪出宫,他们永远“失业”了。李挺梁拿朝廷俸禄,一生积蓄颇丰,可是唯一的儿子却因为染上了鸦片瘾,几乎败光了所有家产,晚年只好卖画为生。
“1933年,为了养家糊口,我爷爷王竹坪和二爷王松坪在琉璃厂紧邻荣宝斋西侧,开了一家清妙斋,以绘画和卖画为生。那时候社会动荡,不少画家生活落魄,把画拿到在这里卖,爷爷也尽量周济他们,无论谁家没有嚼股了,爷爷都会慷慨解囊,不求回报。”
因为李挺梁宫廷画师的名头不少人听说过,大家戏称他为“四朝遗老”,所以画店一度生意不错,汇集了不少画家名流。王伟曾听爷爷说起一件趣事,当年张伯驹也是画店的常客,他倾尽家财收藏名画文物,一次看中一件宝贝却囊中羞涩,跑到画店里借了200块钱才买下了这幅画,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也来店里和王竹坪切磋过工笔花鸟画的技法。

解放初王竹坪在进行绘画创作
特殊时期悄悄传习宫廷画技艺
1943年,李挺良以91岁高龄去世,一代宫廷画师离去了,然而关于宫廷画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解放以后,清妙斋公私合营归了国家,我爷爷王竹坪也成了上班族,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负责画卫生宣传画,这也算是把过去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手艺用于服务社会大众了。”王伟记得,爷爷当时工作很认真,画了不少贴在街头的宣传画,例如积极打苍蝇灭蚊子除四害等等,“即使宣传画也能看出宫廷画那种工笔重彩的风格,设色很讲究。”
1958年,王竹坪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校做教师,教授工笔重彩花卉,在这里他度过了快乐的10年,因为终于可以把技艺传给更多的人。他的学生中有田雨霖、贺伯英、张同禄等,都是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师。他的女儿女婿王玉文和赵华是宫廷画的家族传承人,如今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制作的彩绘磁盘和鼻烟壶等工艺品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
然而,一场浩劫的到来,却使宫廷画技艺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当初姑老祖和爷爷珍藏了一些古画,为了避祸,爷爷忍痛把画的落款裁掉,后来终于还是遗失了,家中一些古董尽数被砸被毁。”这种曾经服务于宫廷的绘画显然属于四旧,于是技艺只能在家人中间悄悄传习。
所幸家族中有不少人爱画,王伟更是跟随爷爷学画,“我们家当时一共6个孩子跟着爷爷学画,每天3篇小字,5篇大字,一张画,这是功课,不作完不能吃饭,要求极其严格。”多年的艰苦训练,王伟对这项技艺越来越痴迷,他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研习画艺。
如今,王伟正在为家传的宫廷绘画技艺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认为宫廷绘画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具有和其他绘画不同的艺术韵味与精神内涵,它是韵味与力量的统一,并非仅仅是通过指掌的运动就可以完成的,它包括:心、眼、法,笔、墨、色的运用。”
王伟告诉我,宫廷画法中有一个特殊技艺,叫做“三矾九染”,为了使画面颜色薄而均匀,层次丰富,要一遍一遍的晕染,干了再然,至少染9次,甚至更多。“利用时间的推移,意志的磨练最终达到宫廷画派完美的效果。”
这种精神也许正是宫廷画得以传承至今的原因,饱经磨难,历久弥香。

郎世宁的八骏图
郎世宁:最著名的洋画师
在清代宫廷画师中,最著名的要数郎世宁。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郎世宁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康熙最初设如意馆的目的是为研究陈列、西方的科技成果,建成后成为清朝以绘画供奉于皇室的一个服务性机构),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
郎世宁教士1715年七月抵中国,11月获康熙皇帝召见。当时康熙61岁,酷爱艺术与科学,虽然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看待,甚为礼遇。没多久,康熙派郎世宁为宫廷画师,不给他传教的机会。于是郎世宁每日清晨从北京东华门附近的寓所步行进宫,七时向宫门禁卫报到。除绘画外,他还要修习汉文与满文。
他向康熙皇帝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因而受到皇帝的喜欢。康熙去世后,郎世宁继续在宫里担任画师,而且郎世宁还根据雍正的旨意,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孙威凤、王珓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在清朝的宫廷内也开始流行。
雍正时期,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
乾隆皇帝雅好书画诗文,在位期间重视宫廷绘画的发展,所以从康熙时就入宫的画家郎世宁仍然得到重用,成为宫廷画家中的佼佼者。乾隆登基时年24岁,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乾隆皇帝曾让他描绘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乾隆仅在该画完竣、七十万寿及让位时看过此画三次。随即将画密封于盒内,旨谕有谁窃视此画,必凌迟处死。这是郎世宁所绘二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
郎世宁于1766年去世,年78岁,丧礼备极哀荣,葬于城外数公里御赐的一块土地上,乾隆还亲撰墓志铭,以示对这位高年教士永远怀念。郎世宁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在《清史稿》里这样评价它:“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缪素筠:为慈禧代笔的女画师
慈禧太后为拉拢一些亲近大臣,常恩赐一些书画作品,得之者视为殊荣。慈禧太后在其字画上均盖有“慈禧太后御笔之宝”玺印。其实,这些作品全都出自她的“代笔人”——清末才女缪素筠之手。《绮情楼杂记·女画家缪太太》记载,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大臣,但其画技不佳,故召缪嘉蕙进宫,代其作画。”
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出身于云南昆明郊区的一户书香门第。少女时代便擅长书法、绘画,有“女红艺杰”之称。
1889年(光绪十五年)秋冬之交,慈禧降旨各省监抚,通令荐举民间精于翰墨、绘画的妇女,进宫为其“伴闲”。缪素筠被举荐,通过省衙“褒禀”后,很快被应召赴京。经过“面试”,被慈禧认可,封为“御廷女官”。慈禧常命缪素筠代画花鸟鱼虫条屏及山水、人物扇面,赏赐给宠臣亲宦。代书“福”、“寿”、“禄”等斗方大字,挂于宫殿之内。1894年(光绪二十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诞,凡大臣奉赠寿礼,“皇太后”一律以缪素筠创作的“御笔之宝”回赏,并在字画上加“万岁”二字。由于数多量大,一些不知内情的高官国戚,难免狐疑起来:慈禧哪有这等精力?通过“探底”,方才知悉缪素筠这个“代笔人”。
后来,缪素筠为慈禧太后代笔的事成为“公开的秘密”。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写到,1903年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诗人樊增祥(字樊山),“他正月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举荐我,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自然是婉辞了。
因为特殊的原因,缪素筠对自己这段时间的作品有自己的认识:“泼墨虽多,尽为落套俗题。默默向世,无人评点异议。”但是,这段时间缪素筠居于深宫,见识到历代名家高手的颇多藏品,对她吸取精粹,开拓视野,充实自己,确实受益匪浅。
如今,随着收藏界对慈禧作品的热衷,幕后的代表人缪素筠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宫廷画师绘制《皇清职贡图》
清代民族及异域风情全景图
如今飞机、高铁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拉近了两地间的距离,“从此山不在高,路不再漫长”,若打算去云南、新疆、西藏感受一下少数民族风情不算什么难事儿。这在以前就很困难,搁到古代甭说是老百姓,就是万岁爷去趟边疆也不是轻易能动身的。为此清代乾隆皇帝在264年前干了一件大事儿,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初一日颁降谕旨:“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侍,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地方官员把自己地盘内少数民族的相貌服饰,风俗习惯统统画下来送到宫廷。于是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珍贵的《皇清职贡图》。
乾隆决定绘制《皇清职贡图》
乾隆爷可不是心血来潮,图个新鲜,才闹出这么大动静。清朝经过励精图治,到了乾隆这一代,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普免钱粮,兴修水利,保护农业,社会稳定。开疆扩土,平定叛乱,完善统治,统一国家。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治军事繁荣昌盛,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面对不断扩大的疆域和不断归附的少数民族,此时的乾隆爷想要见识一下偏远地区“子民”的模样了,一来展示一下大清朝对众多民族怀柔政策,二来显示一下大清朝唯我独尊、万国来朝的派头。便下令“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
给皇上办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弄个“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据《四库全书·提要》说,各地画匠“或奉贽贡篚,亲睹其人;或仗钺乘轺,实经其地。”总之是真实写照,降低失真,力求保真。可是在自己的辖区内自己做主还好办,《皇清职贡图》中“西洋”部分就要下点功夫了。为此乾隆爷大开方便之门,先让宫廷画师描绘出自己接见外国使节的图像。清宫《活计档》曾记载乾隆十六年“缅甸国人朝觐行礼,着海(望)带领丁观鹏将伊形式服色看画”,后又搬出欧洲在中国的“订烧瓷”以及康熙朝的“画珐琅”,让画师借鉴其中西洋人物形象。现在的《皇清职贡图》第一卷大西洋部分总带有清宫藏品中西洋人物的影子。
经过六个春秋,《皇清职贡图》基本绘制完成,然而最终结稿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这并非那时候办事效率低下,而是在这前后三十年间,陆续有准噶尔及其统辖下的回疆等地被纳入清朝版图,以及哈萨克、布鲁特等使臣来朝献贡,又有土尔扈特东归等事件发生,作为记述历史的大型画卷《皇清职贡图》当然要不断增补。
明朝末年,瓦剌各部出现内讧,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但是后来沙俄不断大量移民,侵占他们的牧场,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强征兵役。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沙俄的百般欺压,决心离开生活了140多年的异土,不远万里、历时半年,回归祖国。
《皇清职贡图》做了如下的记载:“土尔扈特,旧为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其先世和鄂尔勒克汗,与绰罗斯巴图鲁浑台吉不睦,遂徙入俄罗斯额济勒地。”“三十六年,其子渥巴锡与合族台吉谋,挈全部十万余众归顺。”“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聚谋弃其旧居俄罗斯之额济勒游牧,率属归顺,既允所请。”“而其旧俗罽衣冠,与准噶尔他部不类。并敕增绘,以广前图所未及。”有关土尔扈特人的图像,从台吉(爵名,或为“太子”之音译)、宰桑(官名,或为“宰相”之转音)到民人,男女共六幅,数量之多是《皇清职贡图》中不多见的的。可见乾隆爷对土尔扈特人拳拳之心的褒扬。

宫廷画师最后定稿
事实上,绘制《皇清职贡图》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早在皇帝降旨之前已有铺垫。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二十九日《起居注》记载清圣祖谕旨内已有:“观郎中尤冷格所进图样云,猺人为数不多,栖身之地,亦不宽广。但山险路狭,日间不敢出战,夜间系彼熟径,来犯我军,亦未可知”等语。可见康熙年间郎中尤冷格已进呈广东猺族图样。贵州巡抚陈诜抵任后,也曾就贵州通省土司苗倮地方之居址疆界情形,考察后绘图贴说,进呈御览。
《皇清职贡图》之前曾有过《四川省番图》、《职方会览》等图册,为《皇清职贡图》打下基础,因此乾隆朝才得以制定统一格式,下发图样,收缴样本,最后由宫廷画师统一完成。现藏于北京故宫的同一时期的《万国来朝图》有些少数民族和邦国使者的人物形象与《皇清职贡图》如出一辙,说明这两幅大作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范本。
咱们现在能见到的《皇清职贡图》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卷,为彩绘四卷,满汉对照。一种是册,为九册黑白线刻,汉语说明。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四库全书·皇清职贡图》九卷本,总共绘制三百种不同的民族与地区之人物图像,每一种图像皆描绘男、女二幅,共计约六百幅。细琢磨这些图像你会发现在包括“苗猺黎獞”“外夷番众”等众多国家、民族、部落、族群之中,唯独没有描绘满、汉、蒙古三个大民族。难道乾隆爷脑子也有进水的时候?其实不然,乾隆帝在谕旨中明确说道“我朝统一区宇”,而并没有说“我满洲统一区宇”,那么此处乾隆帝所言的这个“朝”--“大清”是由谁来建立的呢?
回顾一下创建清朝当时的情景,崇德元年(1636)四月于盛京,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宗室王公、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为代表的漠南蒙古诸部领主王公,以及以都元帅孔有德为代表的汉人军阀共同敬上尊号于皇太极,推戴其为“宽温仁圣皇帝”,并以这位皇帝为中心建立了大清政权。毫无疑问大清当政者认为满、汉、蒙古才是“体制内”的人,而《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其他民族。同样被“体制”的民族还有编入八旗的鄂温克、锡伯、达斡尔等民族。
透过《皇清职贡图》我们可以了解少数民族的“性情习俗,服食好尚”,例如《皇清职贡图》卷八对贵州铜仁苗族记载“其俗,五月寅日,夫妇各宿,键户禁语,以避虎伥。”这是啥意思,是描写苗族避白虎鬼,恐致虎伤的禁忌习俗,也可以说是虎崇拜的缘由之一。卷四对连州瑶族这样写道:“蓄发为髻,红布缠头,喜插鸡翎。性凶悍不驯。…瑶妇衣尚刺绣,皆自为之,青帕蒙头,饰以簪珥。常著芒鞋登山樵採。婚姻以唱歌相谐。”
在这里描写了瑶族的性格、服饰、手艺、婚姻、习俗。可是在描绘少数民族的同时大清朝还是表现出一种天然优越感,总给人一种少数民族茹毛饮血、青面獠牙不受待见的感觉。这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不难看出。全篇充满了带有反犬旁的“俍人”、“仡佬”“倮倮”、“仲人”“僚”“俅”“倧”等文字。其实这表现了满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个问题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制订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皇清职贡图》的价值
职贡图不是清代的独创,却是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提要》说:“考《南史》载梁武帝使裴子野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荒服至海表凡二十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梁元帝有《职贡图》。史绳祖《学斋占毕》引李公麟云,元帝镇荆州,作《职贡图》,状其形而识其土俗,凡三十馀国。” 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代梁元帝萧绎所画(宋摹本)。适逢羊年,我们发现“羊”的形象最早就出现在职贡图上。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朝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被认为是已知最早出现羊这一形象的绘画作品。该画所描绘的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另外唐代绘画周昉的《蛮夷执贡图》,也出现了羊的形象,一胡服贡使,手牵一头长角羊向大唐进贡。进而有人根据史料记载外国贡物清册,推断这只长角羊应当是一只剑羚。我国对羊只有“绵羊”“山羊”之分,顶多再有地区之别,外国则将羊的不同品种分别命名,难怪中国的“羊年”忙坏了老外的翻译们。这是题外话了。
依照惯例,职贡图是记录朝廷与其他藩国或者地方的朝贡关系,事实上乾隆朝职贡图“西洋”部分,有些邦国与朝廷仅有互市贸易关系,把这些邦国均纳入职贡范畴是乾隆爷“唯我独大”的心里体现。中国古代王朝一直以天下中心自居,将周边民族或国外都视为外藩臣属,它们与中国的交往都是对“天朝”的职贡。与南北朝时代梁元帝萧绎所画《职贡图》相比对,那时候描绘供者恭恭敬敬,鱼贯而立。
到了清代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通过成对男女形象手持珍奇宝物梯次来朝,可是没有改变的还是盲目的自我中心。要表现出这种“中心”意识就必定不可将“西洋”排除在“职贡”范围之外。因此乾隆朝的职贡图便涵盖了所有能搜集到的“西洋”与“夷人”。只是做老大不但要有老大的胸襟与气度,还要有老大的实力与行动。否则还是逃不脱清代逐渐衰败、被动挨打的结果。
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皇清职贡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图像与文字资料,艺术家看到绘画,史学家看到历史,民俗学者看到了风土,经济学者看到物产,民族学者看到部族,语言学者看到满语,我们老百姓则看到了二百多年前的众多民族生活状态和习俗。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