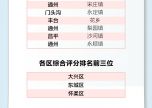如今的月坛周边,有两条主要的大道:月坛北街和月坛南街。这两条路的前身就是月坛的坛墙向不同方向延伸出来的两条繁忙小道,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城市建设,这两条小道不断拓展而得名月坛北街和月坛南街。拓展后的这两条街也沿袭了昔日的热闹。不过,在历史长河里,有的街道一直繁盛,有的街道慢慢衰落,比如,紧挨着月坛坛墙的月坛东西夹道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作者 张国庆

月坛
月坛南北两条小道能到钓鱼台
月坛南街与月坛北街都是因为紧挨着月坛而起的街名。这两条街道的来历都是有根有影,不过,这两条街的前世不尽相同。
月坛北街的根基是月坛内坛墙北天门(现公园北门)外的甬路。这条甬路与东坛墙拐角处在同一条线上。越过坛墙外边瓜市营房南部边缘两排十几个院落,就是1952年冬至1953年春新开的城墙豁口和新架的大木桥。甬路往西出坛墙即是南营房南部边缘的菜园、农田、粪场、坟地,可到钓鱼台的北部。1953年起,这里开始着手清理菜园、农田、粪场、平整坟地,搬迁部分民居,沿整个这趟线开僻出来的从无到有的新马路为后来又展宽了的月坛北街奠定了基础。
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机关大院陆续在这条新马路的西半段兴建起来。有的大院的礼堂还对外营业。如计委礼堂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这里看过《运虎记》等多部中外电影和《打狗劝夫》、《井台会》等评剧。后来又有了商店、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也成了一条繁华街道。这条路很多年不知道名称,正式叫月坛北街大概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事吧。
月坛南街的其前身有二,一个是月坛东坛墙外原先有一个大菜园子(现为月坛体育场),北起瓜市营房南侧,南至月坛东南犄角。因此,周姓东家被称为坛角周。周家菜园子的南边有一条荒凉大沟,向东至护城河。天旱时是一条干沟,雨季变成河沟,既可排水也能摸鱼逮泥鳅。虽然是一条沟,但是当地人却叫它大胡同子。再一个是,从月坛南门往西至三里河有一条名为乐道湾(在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出版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上标有路名)的荒僻小路。别看道路荒僻,可是从瓜市营房和真武庙左近到钓鱼台去玩的捷径。
路东口的左右,分别有一个桃园子,一家石灰厂(东家姓吕,都称为石灰吕记),还有一家制作绿豆制品如粉丝、团粉、凉粉、豆汁等的粉坊。我家住在瓜市营房时,不止一次到粉坊去买东西,到桃园去买被雹子砸伤的桃,尽管外观不太好看,可是便宜也不烂,挑好些的送人,次的留下自己吃,那也很高兴,毕竟是桃嘛。
小路往西,菜地、荒地、坟地相杂,住户极少,过了铁道住家户才多起来。到了三里河与沙沟,成了回民的聚居地。三里河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围寺而居是回民的习惯。这座坐西朝东的清真寺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重修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寺门石额镌刻“清真礼拜永寿寺”。如今仅存大殿和南、北讲堂等建筑,现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桃园子归到月坛里了。再后来填平了大沟,修成马路。乐道湾同时得到改造,拓宽了路面。随着三里河一带盖起了一些部委的大楼,沿路的商店和住户多了起来。那时开通的13路公交车,从组建至今一直跑这趟线。
当时,马路修建后不久,这里就有了即能看电影又可以看戏和文艺演出的三里河工人俱乐部。我第一次看《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这里看的。后来,这里又盖起了贵阳饭店等大饭店、宾馆、百货商场,公交车的线路也不断增加。一条荒僻的小路和大沟,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如今成了繁华的大街。其实,这条路有好多年头叫社会路。后来,有了月坛北街的街名,也就有了月坛南街的街名。

月坛南街
月坛夹道被误传为谭家胡同
“夹道”者,按《现代汉语词典》解:“左右都有墙壁等的狭窄道路。”月坛东、西夹道,就是指旧时一侧为月坛的坛墙,一侧为民居的两条街道。
这两条夹道路面都相当狭窄,具体位置在月坛东北角的大角门(约现南礼士路42号楼附近)至月坛牌楼之间原光恒街(因属月坛内,故无街名牌,自有月坛菜市后,街名被代替了)两侧坛墙的外边。东边的叫月坛东夹道,西边的叫月坛西夹道,从前在临街口的墙上都钉有正式路牌。当地人为了说着顺嘴,就简化为东坛夹道、西坛夹道,或统称为坛夹道。由此,有不明所以凭听音而辨字者,就揣测出了檀家道胡同。近年,更有人演绎出谭家胡同。在我的记忆中,阜外大街绝对没有檀家道胡同,更没有谭家胡同。特此予以纠正。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就出生在月坛西夹道。我父亲略长大一些后,我家搬到月坛东夹道16号(约现南礼士路38号楼北半部),我祖父的表哥陈二巴巴(读“把”音,回族称爷爷亦为巴巴)家的院里。1939年冬,我出生在这个院子的西屋,屋后檐墙外就是夹道。此院北、西两面都是以屋子后檐墙代替院墙。北屋、西屋、院门有墙相连。
月坛东夹道确实很窄,道东侧是民居,院门都对着东坛墙。路窄得只能通过洋车、三轮车、自行车和井窝子送水的水车。我家院外北边紧邻着一个形状如歪把儿梨的大漫坡(约现华远大厦南端及附近小区大门位置),把整条夹道分成两段。坡北至街口,坛墙已拆到半截,里侧是月坛菜市路东几家菜行的后檐墙。大漫坡的南北两侧也有几户人家,门牌上也写的是月坛东夹道。坡的最上端,即“梨把儿”部分有一条更窄的无名小胡同,可通到老南礼士路。东夹道的最南端与大角门东侧坛墙外的无名小胡同相接,可视为东夹道的延长部分。在大角门往东还有一条无名小胡同,也通到老南礼士路。到我出生时,从我家往南的坛墙已经拆没了,家家院门直接对着光恒街。站在街边上,有的地方还能看到墙根部位裸露着的包墙城砖。由于整条夹道的地势是北低南高,因而由我家往南,地面要比光恒街高出四、五尺。由于人们长年累月地往这一段坛墙根儿倒炉灰、脏土而形成了约45度的斜坡。每到冬天又因不断有人倒脏水而结成冰坡,有的孩子不管脏净把这里当成了滑梯玩儿。
大漫坡与光恒街相接处的路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时称“官茅房”。在日本鬼子投降前,我在这官茅房旁边受过一回罪。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祖母带我要上大街。刚一出院门,就看见陈家二娘儿(回族称姑姑为娘儿,陈二巴巴的二闺女)在茅房那边一个劲地向我们娘儿俩摆手,意思是让我们赶紧回院里去。我们正要转身,被守在茅房边上的日本兵看见了,又拉枪栓又威胁地让我们快点过去。原来,这一溜儿又戒严了。一个赶牛车掏粪的老头正在掏粪。日本兵既不让他继续掏,也不让把敞开的蓄粪池的盖儿盖上。住在坡上的刘家舅奶奶(我祖母姥姥家的弟妹)端着一碗打卤面要上菜市给老伴送去。老太太出了家门刚要下坡。大伙赶紧挥手让她快回家。老太太一时没明白怎么意思,正在打愣。那个小鬼子就拉枪栓连吼带吓唬地让老太太下坡到茅房旁边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时就见好些鬼子兵、伪军、伪警察端着枪,从南边跑过来,挨着家儿地往里闯。最后从我家院子里跑出来,分成两路奔上坡、奔北边跑了。原来,刚才戒严是鬼子在搜捕八路军的探子。结果,鬼子什么也没搜着,我们白挨了一场惊吓。特别是我们刚才被强迫着在粪池边上站了一个多钟头,都被熏得够呛。

月坛
西夹道应有尽有
与大漫坡隔着光恒街斜对面的地方,是西坛墙一处最大的豁口(约现阜成门宾馆位置)。那时,西坛墙也已坍塌成几段,残留的墙体时刻都有再塌的可能。过了这个大缺口就是月坛西夹道了,这里可通到阜外大街南营房,往西南方向可达三里河、钓鱼台。紧靠豁口里侧南边,有一家小茶酒馆。外边放着几张白茬桌子和条凳,常有遛鸟和架鹰的主儿在这儿歇腿儿海聊。旁边还有一个只卖清油大饼、炸丸子的摊儿。把口北边,是卖烟酒、花生瓜子等炒货、核桃栗子枣等干果,冬天增添烤白薯的赵记小铺。再加上路东的官茅房,嘿,这个从东到西不足二十步远的有点儿斜的小小十字路口吃喝拉撒全能解决了。
西夹道比东夹道略宽一些,能通行大车。因为全是土路,冬天深深的车辙冻得硌脚,夏天雨后又成了一溜泥塘,所以一般人除了到夹道路西的小鼎和(后改称小天丰)酱园子买东西的,大都进豁口,走光恒街。这个大豁口把西夹道也分成南北两段。北半段从街口往南依次是,牌楼旁边的一座二层小楼、一处由破旧古庙的大殿改建成的大屋,这里是供菜市职工活动的场所,其南侧就是那个前店后厂的酱园子,没有其他民居。西夹道的民居集中在大豁口迤南至月坛北坛墙外和西夹道与南营房相交的地段。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有一位长大后成为京剧名角再成为开创一个艺术流派一代宗师的人物在月坛西夹道诞生了。这就是京剧马派艺术创始人马连良大师。这是我的祖母在世时不止一次告诉我的。怹的亲娘儿(即姑姑)就是马先生的生身之母。怹与马先生是姑表姐弟关系。祖母说:“你(表)舅爷爷(即马先生)成名后有钱了,就在城里置了产业搬走了。”我记得,祖母有几次带我到位于西单牌楼报子街的马府去看望过怹的娘儿(我管叫姑老祖儿)。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阜外大街及月坛周边地区大规模改建工程的开始,月坛西夹道残留的坛墙率先被全部拆除了,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月坛西夹道完全消失了。月坛菜市迁走后,坛牌楼与月坛的四面外坛墙相继拆除,从阜外大街可以直达复兴门外了。月坛东夹道的民居院门直接对的是新南礼士路了。80年代末期,我多次从这里经过时,还能看到我出生的那间屋子。进入90年代后,一个没留神,月坛东夹道的一大溜平房全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全是新楼房的小区了。月坛东、西夹道连同古老的光恒街彻底从北京市的地图上消逝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