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首都博物馆西夏文物精品展“贺兰山下‘桃花石’”落下帷幕。这是西夏王陵申遗成功后,西夏文物的首场集结,人们在大饱眼福之余,不免感叹,对如此灿烂又神秘的西夏,实在是相见恨晚。
贺兰山下,大漠苍凉,西夏王朝曾存续189年,疆域达115万平方公里。一场灭绝性报复,让一切灰飞烟灭,连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它的踪迹。
曾几何时,“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从1971年发现西夏王陵开始,我们才一点一滴,重新寻回了这一文明。经过50多年积累,西夏已不那么神秘,反而成了破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钥匙。

夕阳中,西夏王陵的1号和2号帝陵。

俗称“妙音鸟”的迦陵频伽
贺兰山下“桃花石”
迦陵频伽是梵语Kalavinka的音译,意为“妙音鸟”。它是佛教中的神鸟,人首鸟身,声音非常好听。佛经说,除了如来的声音,再没有比迦陵频伽的歌声更美妙动听的了。叶嘉莹先生号迦陵,便是出于此典故。《北派盗墓笔记》中,一众高手在黑水城回关,所得宝贝之一,就是它。
在“贺兰山下‘桃花石’”中,展示了各式各样的迦陵频伽。
西夏崇尚佛教,那一时期的迦陵频伽,既保留了佛教“妙音鸟”的本义,又融入了党项民族的审美特色。
一尊绿釉迦陵频伽,神态静谧安详。长圆脸,双颊丰腴,细眉长眼,眼帘低垂,双眉间有白毫,高鼻,嘴巴细小,带有明显的党项人特征。
这些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在西夏王陵,它们主要位于屋顶垂脊和戗脊,作为脊兽中的神兽之首,相当于故宫屋脊上打头的那个“骑凤仙人”。
在北宋的《营造法式》一书中,迦陵频伽又作“嫔伽”,是高等级建筑上常见的装饰,与铜铃组合使用,象征西方极乐世界的“妙音”。明代道教得以发展,“仙人骑凤”才逐渐替代了妙音鸟,成为屋顶上的主要装饰。
这些妙音鸟,随西夏王朝宏伟的陵阙归于黄土,又在残存的瓦当与琉璃中,重新拼合,再现神韵。观展时,与它们相遇,耳畔仿佛响起了穿越千年的妙音。
此次展览中,和妙音鸟组团来京的,共有103件(套)西夏文物,其中三分之一为国家一级文物,展品类型涵盖瓷器、金银器、碑刻、雕塑、建筑构件等,绝大多数来自西夏陵,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西夏文物展之一。
它们不仅是对西夏文明的系统回顾,也是今年西夏王陵申遗成功后,对“何以西夏陵”的解答。
鎏金铜牛,出土于陵区一个贵族陪葬墓,是一件青铜铸造的珍品。它呈卧姿,四肢蜷曲,体形魁梧,目光炯炯又极为平静地注视着前方。这个造型生动逼真、工艺高超的“国宝级”文物如今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除建筑构件外,西夏王陵保存下来的文物相对稀少,每一件都堪称精品,这件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在辽宋夏金时期,如此大的鎏金雕塑极为少见,它既体现了西夏从游牧到农耕社会的转变,又表现出西夏对中原技术的发扬。

西夏鎏金铜牛
银川宏佛塔出土的佛头,面部圆润饱满,线条大气,富有唐代造像遗风,是西夏吸收继承唐文化的典型物证。佛头眼珠内的黑色釉料因高温而溢出,好像悲悯世间疾苦流下的眼泪,慈悲感拉满。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刷品竟然是西夏文的。《梦溪笔谈》记载,活字印刷术由北宋工匠毕昇发明,但一直没有出土相应的印本佐证这一史实,个别国际学者甚至对起源产生了怀疑。直到1991年,拜寺沟方塔出土了西夏文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才算有了实物证据,而且是比泥活字更先进的木活字。
这一印本,精美堪比宋刻,当中的西夏文字方方正正,也有横竖撇捺,偏旁部首,却只是似曾相识。它们繁复、对称、工整,曾因无人能识,而被称为“天书”。
凝视这些展品,让人不由产生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西夏文字到绘画,从佛教造像到建筑构件,既有对唐宋文化的借鉴,又富于自身特色。
这也是本次展览那个美丽的名字——“桃花石”的由来。王效军对记者说,“桃花石”一词普遍出现在回鹘突厥文献中,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13世纪初的《长春真人西游记》。
“该词是当时中亚对中国的统称,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体现了他们对中国的高度概括和认同。”
大唐之后,辽宋夏金共铸“中国版图”、共承“中国之制”,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因此,在他者的视野中,辽宋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被统称为“桃花石”。
“西夏虽在西北,但依然有着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西夏积极融入中华文明主流,这就为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了独特贡献。” 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他做了多年讲解工作,日日与文物相伴,这是他最深的感悟。
成吉思汗的“遗诏”
虽然同属“桃花石”,但相对于大宋辽金,西夏显得神秘低调得多。它由党项人创立,自称“大白高国”,前期和辽、北宋,后期与金、南宋并立,共历经189年(1038年—1227年)。
这个与宋辽、宋金都形成“三国鼎立”格局的王朝,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足有115万平方公里,还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为什么被遗忘了数百年?为什么连二十四史中都没有专史记载?以至于很多人与西夏的初识,都是因为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虚竹娶了西夏公主。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战说起。
1227年,黄河边上的六盘山。帐外,十万蒙古铁骑已将西夏都城团团围住;帐内,这位66岁的征服者却已病入膏肓。
从1205年起,蒙古与西夏,在长达二十多年间,6次交锋,其中有4次是成吉思汗带兵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出兵助战为由,发动了最后一次征讨。此时的蒙古帝国已横跨欧亚,但从草原走出的征服者,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六盘山营帐中,成吉思汗向儿子们交代后事。波斯人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了成吉思汗的遗诏:“我死后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他们从城里出来时,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攻陷中兴府(今银川市),将城内十几万党项人全部屠杀,西夏从此灰飞烟灭。
《元史·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之死和西夏灭亡的记载非常简略,甚至有些隐晦,对中兴府的屠杀更是避而不谈。一些宋人笔记和后来的史书,则用了“殄灭无遗”“民庶穿凿土石,避锋锐,免者百无一二”等语,可见屠城之惨。
多年战争结下的梁子,西夏的拒而不降,再加上大汗之死,使蒙古铁骑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报复行动。
由于成吉思汗的战略意图不仅是征服,而且要彻底摧毁西夏这个政治实体和文化民族。因此,屠杀还包括对西夏皇室、贵族、文臣武将乃至知识分子的系统性清除。战后,西夏文字、文化几乎全被摧毁,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场毁灭的彻底性。
在蒙古征服史上,对投降的国王或者统治者,并没有杀掉的先例,只有西夏末帝除外,对党项人的决绝,由此可见一斑。
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党项人的故地——唐兀特。在马可·波罗之后,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命到中兴府一带兴修水利。郭守敬发现,曾经农业发达的宁夏平原,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地。
公元1288年,忽必烈改中兴府为宁夏路。宁夏者,夏地安宁也,此名一直沿用至今。中国都是后面的朝代给前一代修史,元给宋、辽、金都编修了正史,却唯独忽略了西夏,这又是一种刻意抹杀。
到明朝中期,西夏的影子越来越模糊,逐渐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不过,存在过的东西,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在北京北郊的居庸关,有个用汉白玉砌成的精美云台。云台上有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用6种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1863年,有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云台上的刻字,其中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早就被确认了,但有一种方块字却难住了中外专家。
10年后,才有英国学者提出,这种文字应该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1882年,有研究过女真文的法国学者说,这也许是西夏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898年比较了“凉州碑”后,才得到学界认可。
仅认定西夏文,就经历了35年,不要说对这种文字进行解读了。西方汉学家能确定这是西夏文,也是参考了清代史学家张澍的研究。
1804年,张澍因病从贵州回甘肃省武威老家休养。在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时,他在一座碑亭内发现了用砖封砌数百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拆除护砖,一通高2.5米的石碑重见天日,正面是总字数达1820字的“天书”,背面则是与之相对照的汉文楷书。他考察了汉文碑文中所书的年号“天祐民安”,方知其为西夏文。
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造字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逐渐成了死文字,通过这块碑,虽然复活了一些西夏字,但仅靠这千把字,不仅无法一窥西夏的究竟,反而使其更显神秘。
“黑水城”宝藏的遗憾
西夏学兴起,不能不提黑水城往事。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这座古城早已被风沙吞没,但在西夏统治时期,它是边防重镇。
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攻黑水城,守城的黑将军英勇善战,使蒙古军久攻不下。后来,蒙军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截断了城内的水源。黑将军在城内掘井求水,却始终找不到水。绝境之下,黑将军将所有的金银财宝埋藏在一口深井之中,然后杀出一条血路,与蒙古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最终全军覆没。
为了寻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苦寻黑水城。1908年,他不仅找到了这座废城,还在一座被密封的塔里,发掘出一座西夏“图书馆”。大量西夏文刻本、写本,包括佛经、字典、辞书、法典、文书,几乎应有尽有,40峰骆驼都不足以驮走所有文物。此后,洗劫过敦煌的斯坦因也相继到来,他们都不是考古,而是赤裸裸地盗掘。
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起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三大地下文献发现。同敦煌遗书一样,黑水城文献一出土便流失海外,外国学者占得先机,我国学者却无缘一见。
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这些文献时,发现了一本奇书,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
这是一本夏汉对音对义的词语集,涉及不重复的西夏字1504个,前两页是汉文、西夏文对应的序言,倡导党项民族和汉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其后数章,按一定顺序收录各类词语,并在“人事下”一章中虚构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的经历,把与每一事件相关的词语插入其中,可诵读成文。
金石学家罗振玉想方设法,终于从伊凤阁处拿到了这本“双语对照教材”的全部照片,并让其长子罗福成抄写后校勘出版,这就是曾在西夏学界流通甚广的“罗抄本”。
“我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1915年罗福成撰《西夏国书类编》,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译释和研究。”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说。
罗家父子之后,西夏学慢热起来,中国社科院的王静如老先生,还曾招过西夏学研究生,史金波便是他的第一个学生。现在,史金波已成为西夏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这门“绝学”刚有点起色,就在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此时,苏、日、英的西夏学研究却硕果迭出,以致有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
正是这一说法,激发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斗志。为了掌握这门“绝学”,李范文放弃了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主动要求到宁夏去,到西夏故地去。
1960年6月,当他意气风发地到了宁夏,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等待他的,是巨大的失落和挫伤——此时,宁夏不仅没有任何西夏研究单位可去,更无西夏文献资料可查。
何去何从?他只得先栖身于宁夏大学历史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贺兰山不是去研究,不是去游玩,而是单位组织大家漫山遍野地采榆树叶子充饥。
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见到一些西夏文献。总理立刻询问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还有没有人懂得这种文字?”王冶秋答:“据说仅有一两位老人能懂。”总理立即指示:“你们要培养一些人学这种西夏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借此机会,李范文调进了宁夏展览馆(宁夏博物馆前身)。他等了12年,蹉跎了12年,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研究西夏文了。然而,此时的西夏学,门可罗雀,冷得堪比贺兰山的雪。
“扫地僧”为王陵正名
黑水城文献像一束光,照亮了西夏历史上长达700年的暗夜,人们知道得越多,越想寻找物证。他们创造的文明在哪儿?真就被成吉思汗“一键删除”了吗?
1937年,当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时,或许未曾想到,自己镜头下偶然捕捉到的景象,将成为叩开一个失落王朝大门的伏笔。
在他的《中国飞行》一书中,记录下了山脚下连绵起伏的圆锥形“土堆”,它们在苍茫的戈壁上沉默着,仿佛是写给天空的谜语。这是美洲白蚁堆?还是史前文明?一些追问,轻飘飘地在书中掠过。

20世纪30年代3号陵德国飞行员航拍图
20世纪60年代末,陕西考古所的刘最长坐长途车途经这里,只匆匆一瞥,他就觉得这些气势恢宏的土堆不一般。凭借考古人员的敏感,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唐墓。
两年后,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小旅馆里,他对西北大学的老同学钟侃随口谈道:“贺兰山底下的那些陵墓很大啊,是唐墓吧?没被盗吧?” 一连串问题让钟侃立马郁闷了:“我在宁夏待了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还有个唐墓?”
1971年底,为了验证同行的这一猜想,宁夏展览馆的钟侃和他的同事们,爬上一辆跃进牌卡车,身披老羊皮袄,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贺兰山下去踏访。
当时这里还是空军基地,一道深深的掩体旁,堆积着翻上来的砂土碎石,里面混杂着红色砂岩石块。钟侃眼前一亮,这分明是残碑。他们在碎块中仔细翻找,一块有文字的石头映入眼帘。
这些残碑上的文字既不是史前遗迹,也不是唐朝文字。钟侃因参与过青铜峡108塔的考古,见过西夏文的经卷,认出这就是西夏文。
带着这些“土堆”可能是西夏陵的期待,他们一头扎进史料中。最终,在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找到了线索:“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难道这就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踪的西夏王陵?正踌躇间,空军基地又传来消息,修机场时挖出了陶器和奇怪的文字碎片。
钟侃再次带队赶到距银川市40公里的工地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由于多次被盗,墓中并未出土有价值的文物,但精美的壁画仍让考古队感到震惊,根据壁画上描绘的武士、花纹,以及墓葬的形制,考古专家断定这是一座西夏时期的墓葬。
地毯式勘探发现,贺兰山下共有15座带有封土的大型陵墓,其中9座是帝陵格局,此外,还有陪葬墓二百余座。
后来被正式命名为6号陵的帝陵,让考古队员足足挖了三年。那深藏于地下25米的墓室加上地面高达16米的陵台,使这座陵墓的整体建筑高度超过40米。甬道内发现的圆木最长的达4米,直径在9到22厘米之间,也可见昔日辉煌。
虽然文献、断碑、墓室,都在宣告西夏王陵重见天日了。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不了——没有铁证。
凌乱不全的人骨、散乱在地的铜门钉泡、武士的鎏金甲片以及被破坏的壁画……显然,这里曾被人有计划地破坏过,出土文物中几乎找不到一件完整成型的器物。
如此疯狂的破坏,以及陵区内无处不在的“大掀顶”式盗洞,根本就不是普通盗墓贼所为。考古学者推测,只有派了军队才能盗掘全部王陵,因为像西夏帝王陵这个规模,挖掘的土方量需要几千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到底是不是蒙古大军毁的呢?无论文献还是近50年的考古,都没发现证据。
残碑上的只言片语,信息浓度最高,但如同天书的西夏文,让考古队员一筹莫展。宁夏真就没人认得这些字吗?答案是,有,而且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身边的“扫地僧”。
西夏陵发掘时,李范文还是个“右派”,不能搞考古,但他自愿去工地当勤杂工。当时全队只有他一个后勤,管理伙食的是他、招收民工的是他、打扫卫生的是他、采购日用品的也是他。
虽然是唯一的后勤,但他的待遇却远不如正式队员,“人家都发皮大衣,一个月发一块肥皂、毛巾,我是编外人员就没有了”。
伴着贺兰山下肆虐的风沙,李范文白天忙“正业”,若有空闲,就着手整理陵区出土的几千块残碑,一丝不苟地编号、拓印和分类。夜晚,他还要把一碑一石中辨识出的只字片语,用三合板做成识字卡片。
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他抱着一只沉甸甸的大木箱,里面是两万多张西夏文卡片。
李范文带着这些资料,刻不容缓地请教于西夏学专家、罗振玉的小儿子罗福颐。罗先生感动于他的真诚与迫切,慷慨地将自家珍藏多年的西夏文献全都借给他抄写。
他还去看望了考古学泰斗夏鼐,那天天色阴沉,夏鼐看他形容憔悴,就指着窗外的天空对他说:“你看这个天不可能永远都是黑的,总有晴的时候。”
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关键的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16个西夏文篆书的含义:“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

6号陵破解出的碑文

李范文
这无可辩驳地证明,7号陵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说明,这个占地约40平方公里,相当于明十三陵体量的墓葬群,就是西夏王陵。
仁孝是西夏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在确认了仁孝的陵墓后,学者们本以为其他陵墓的身份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可是,为王陵编号时,问题出现了,西夏有10位皇帝,但这里只有9座帝陵。至今,其他8座陵墓主人的身份,仍难确认,因为最有价值的陪葬物——墓碑,或者叫墓志,都完全被破坏了。
1977年,发掘一座陪葬墓时,又是空空如也。老专家失望徘徊,愤怒地踢了墙一脚,没想到一脚踢出去,竟然摔了一跤,考古队员还以为他触动了墓中机关,纷纷躲避。回过神来一看,才发现是墓墙与地面的交界处,一个金黄色的“牛角”将专家绊倒了。鎏金铜牛就这样显露了真容,旁边还有一匹看似温顺的石马。
“也许是墓室塌陷,这一牛一马,才得以留存。”党项贵族尚且有如此奢华的陪葬,当年的王陵想必也是“事死如事生”般的厚葬。
在这次发掘之后,西夏王陵再没做过墓室发掘,而是集中在地表清理和大范围测绘上。近年来,防洪工程是西夏王陵考古的重点。

墓道中出土一牛一马

2000年,对3号陵进行了全面的地面发掘。
面壁7年破解“天书”
考古越深入,问号也越多,怎么办?只有先下苦功夫,从了解西夏开始。
从1972年开始,考古人员时常轮换、撤走,但李范文却在西夏王陵待了整整7年。
那时的西夏王陵,不比今日,用边塞诗来形容就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7年里,多少次狂风呼啸,吹得帐篷四角翻飞;多少次暴雨如注,淋得他无处躲避;多少次大雪纷扬,绊得他步履蹒跚;多少次夜半狼嗥,惊得他彻夜难眠。
不仅如此,长期的白水煮面、咸菜就饭,使他营养严重缺乏,以致1.77米的魁梧汉子只剩下了50公斤的体重。
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
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先后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和《西夏研究论集》。
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出近6000个西夏文字,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的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这部耗费20余年心血的巨著正式出版,标志着西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人人可读可看的阶段。
1979年,由钟侃、吴峰云、李范文三人合著的《西夏简史》出版,理清了党项族从诞生、建国、灭亡的历史脉络。
西夏,这个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并非凭空出现。它的根,深植于唐末五代的乱世中。早在贞观年间,党项大首领拓跋赤辞便归顺唐朝,成为西戎州都督,并被赐予皇姓。此后,拓跋李氏世代镇守西北,唐末又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确立了在银夏地区的世袭统治。
经历了后梁、后唐等中原王朝的更迭,夏州政权逐渐“傲视中原”,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在爷爷和爸爸的深厚积淀之上,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李元昊称帝后,刻意强调西夏的正统性,祭祀中原王朝认可的“昊天上帝”,沿用“年号”纪年,仿效唐宋制度推行州县制与官僚体系,通过对中原政治符号和治理模式的主动接纳,提升国家认同。
仁孝推行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他的带领下,国力达到鼎盛,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
史料记载,西夏王陵仿宋陵而作,而宋陵是按照中原传统的昭穆葬法来安排王陵的。按照这种布局,一般是父亲在左边,儿子在右边,下一代再左边,再右边。
根据这种“之字形”葬法,九座王陵由南向北排列,算上李元昊爷爷李继迁和爸爸李德明的墓,到仁孝刚好是第7座王陵,最大的3号陵,则是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墓。
由于陵墓一般是随城兴建,专家推测,最早的兴建者很可能是李元昊的爸爸李德明。从李德明韬光养晦的性格看,一方面他和大宋皇帝不能平起平坐,因此专门建了月城来集中安放石像生;另一方面党项人也需要昭示自己的民族特色。因此,西夏陵与宋陵大体相似,但宋陵是面山背水,而西夏陵则是面水背山,面朝黄河,背靠贺兰山。
这种既想模仿中原,又保持自身特色的矛盾心理,贯穿了西夏文化的始终。
西夏陵出土了十余件驮碑的人像石碑座,它们近似正方体,正面是一个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的大力士形象,两侧是西夏文、汉文。按照中原传统,驮碑的应该是长寿的巨龟(赑屃),但党项崇尚力士,于是这种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特征的人像石碑座,就成了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绝佳例证。
一米五高的鸱吻,是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鸱吻构件之一。其工艺水平不亚于同时期的北宋和辽,证实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的传播,龙头鱼尾造型,粗犷豪放,则是党项人独有的。

绿釉鸱吻
作为西夏陵考古发掘“第一人”,钟侃曾评价道,在中国历史上,西夏陵是地面遗迹保存得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是研究和了解西夏史信息量最大的一处历史文化遗迹。
正如王效军对记者所言,西夏陵及其出土文物作为实物例证,生动地展示了西夏从建筑、文字到政治体制、农业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恰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西夏陵,正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特殊见证”。

墓道中出土一牛一马

2000年,对3号陵进行了全面的地面发掘。
30年来文献“回归”
西夏王陵发现后,文字、文献、文物、遗迹,与西夏历史相关的痕迹慢慢逐一浮现,交织成西夏学研究的新网络。
1987年冬,李范文和史金波作为访问学者到访苏联,到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特藏阅览室阅览西夏文献。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首次亲眼看见黑水城文献的全貌。
这里的西夏文文献,有8000多个编号,约20万面,学术价值极高,但过去刊布的文献极少,很多重要文献长期不为人所知。
李范文忆起内心的波澜,“当时这批文献静静地躺在12个高大的书柜里,有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有的已经残破了,但总体来说,保存得很好。”当时,因为苏联的研究员出现断层,以及经费问题,这些必须通过解读才能展现价值的珍宝,只能“吃灰”。
那年列宁格勒的气温为50年最低,达到-34.7℃。他们两个早出晚归,仅用三个星期就阅览了全部西夏文献。
两个人心愿一致,就是要让这些束之高阁的文献“回归”。经过多方努力,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俄学术部门积极开展合作,整理出版了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截至目前共出版32册,预计2026年出全。
史金波带队,曾分别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四次前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每次逗留约3个月。“我们的工作是将俄藏西夏文献全部拍照带回。当时俄方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工作时间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以支付加班工资的条件让俄方每天延长两个小时工作。”
这项工作至今已持续30余年,可谓旷日持久。这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换了4届领导,《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两位主编克恰诺夫、魏同贤先后去世,史金波也从中年到了耄耋。
同一时期,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胡若飞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帮助下,将英藏黑水城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中国。法、日的西夏文献,也逐步公开出版。
近30年来,原始文献的爆发式出版和大量西夏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西夏学插上翅膀,中国自然成了西夏学的主阵地。
杜建录说,他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用文献阐释西夏社会的历史面貌,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显然更具家国情怀。
今年,杜建录历时10年主编的《西夏通志》出版,煌煌12卷400多万字,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专史之间,他说“这是为了弥补二十四史中无西夏史的缺憾”。
西夏,这个曾活跃于贺兰山下的王朝,虽在蒙古铁骑下湮灭,却以瓷器的剔花纹样、陵墓的夯土高台、黑水城文献,留下了“桃花石”的鲜明印记,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力士人像石碑座
9分钟“申遗”成功
天高野旷,当记者站在西夏3号陵,那座被推测为李元昊泰陵的陵塔前,依然会为它的雄伟与神秘而震撼。
那座曾经高达七层的实心八角密檐塔,虽历经千年风雨,木结构早已荡然无存,但留下的高大夯土建筑,依然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荣耀与沧桑。
那是个遥远的古国,源头为羌人,衍生为党项,牧猎西北,崛起贺兰;
那是个英勇的古国,傲视天下,敢与大宋分庭抗礼而毫不示弱,能与东北辽金鼎足峙立而力挫群雄;
那是个灿烂的古国,以“承唐仿宋”的制度建构为经,以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创造为纬,用开放包容的胸襟,在丝路文化上点石成金;
那是个包容的古国,他们将党项族融入华夏血脉网络,接受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同时容纳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民族共居共融。
3号陵是李元昊墓吗?毁陵的是蒙古大军吗?幸存的西夏人远走何方?如果没有更多证据出现,很多问题将会一直被悬置。
不过,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申遗并无影响。今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直播中,前一个项目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到西夏陵9分钟就过了,没有人提出异议。”在师培轶看来,这个等待了14年的结果,不过是实至名归。
1998年西夏陵博物馆落成,他提前一年被培训为讲解员。30年来,西夏陵获得了最高等级保护,开启了新生之路,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成长。
游客最爱听他讲陵塔“不长草、不落鸟”的故事。其实,保护夯土建筑是世界性难题。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直到2000年国内技术相对成熟时,这里才从本体加固和提高夯土表面抗风化能力两方面入手,探索出了适宜西夏陵的保护方法。
加入申遗预备队后,西夏陵的保护进入了更为精细化的预防性保护阶段。遗址内的每一场雨,每一阵风都被高科技监控着,技术人员每年还会对遗址进行全面“体检”,及时解决出现的小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能在山下矗立近千年而未遭山洪毁坏,离不开王陵建造者当年修筑的32处防洪工程。今人不输古人,更安全的防洪堤坝早已筑起。
文物保护条件更是得到了质的飞跃。师培轶清晰记得,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只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拣而来的残砖断瓦。而到了2019年,新西夏陵博物馆投入使用,恒温恒湿的储藏设施,已能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
展陈手段的迭代,也让西夏文化“活”了起来。不过,师培轶依然每天接待游客,用他那在陵区旷野中练就的大嗓门,向人们讲述着博物馆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一开始不足30件文物,到如今多达近万件的馆藏文物,他每次讲的内容都在更新扩展。
申遗成功后,西夏王陵每日接待人数过万,人们把师培轶馆长团团围住,为这个消失的王朝着迷,也为追寻的历程感叹。正如那些在陵塔上空盘旋又飞走的飞鸟,它们或许不会在此停留,但会将这传奇带向远方。
未来,西夏将不再那么神秘,妙音鸟的故事已经传遍世界。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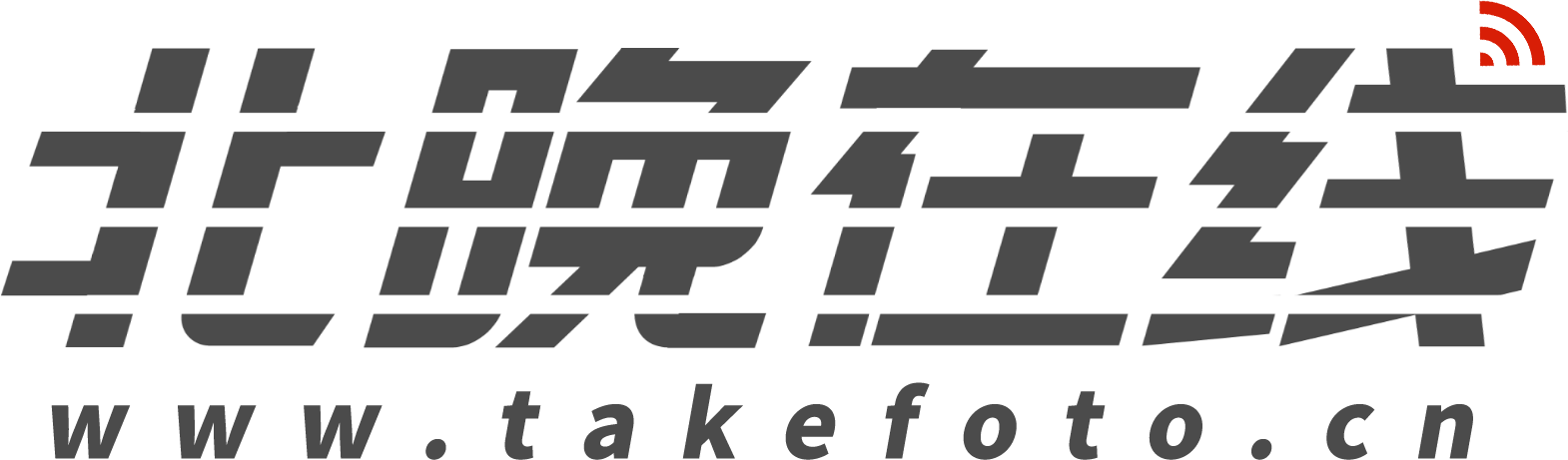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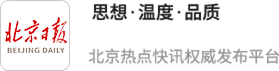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全部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