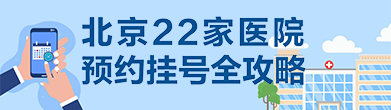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

3C标志换个“马甲”接着卖,网络平台如何管?
6月26日民航局“充电宝新规”一出,“3C”立即成为热门话题。北京日报客户端接到多位消费者反映,网络平台上竟有不少商家售卖“3C贴纸”“3C印章”。记...
北京日报客户端 -

锐评|中国人的团结再一次具象化了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遭遇特大洪水,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眼下洪水逐渐退去,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天灾无情人有情。面对暴雨急流...
北京日报客户端 -

地震遗址收费、钱塘江被围?公安部公布8起网络谣言案
6月27日,公安部公布近期8起典型案例,目前涉案造谣人员均已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川5.12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收费”网络谣言案。四川公安网安部门查明,60岁男子尹某...
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