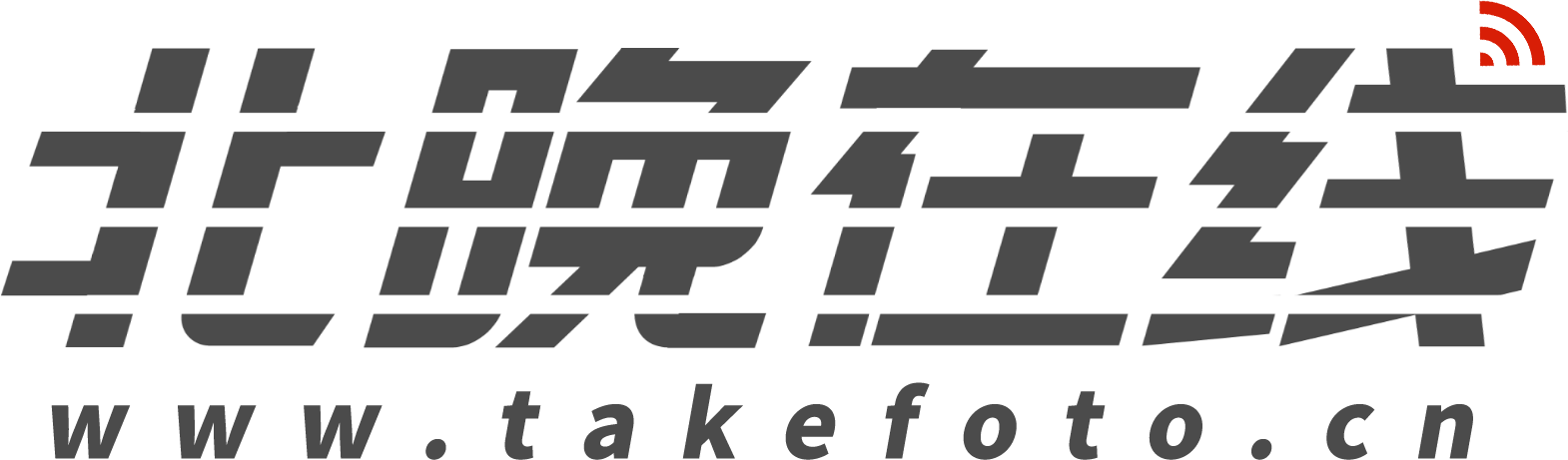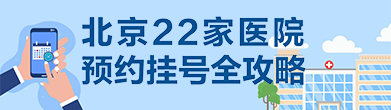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

新华社评可可托海雪豹伤人事件:面对野生动物,不越界是尊重更是安全
1月23日,新疆可可托海,一名滑雪游客在返回宾馆途中被雪豹咬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生活在高海拔山区的雪豹,是大型猫科食肉动物,素以神秘、敏捷闻名。平时难得一见的国...
新华社 -

极限攀岩家登顶后,民进党当局竟给台北101“改名”,引发岛内网民不满
美国极限攀岩家阿历克斯·霍诺德1月25日独攀台北101大楼,历时91分30秒顺利攻顶,成为在未使用任何绳索、安全吊带或降落伞情况下,成功攀登台北101的世界第一人,全球不...
环球时报 -

探访北京旅拍 “格格加工厂” ,火爆背后如何避雷?
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大批游客抵京,少不了去充满中式美学的古建筑游览。红墙绿瓦、古风服饰、绝美留影,在很多人看来,旅行中没有旅拍似乎是不完整的。 记者在节前走访旅拍市场,...
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