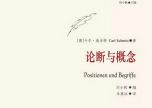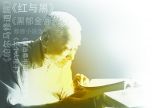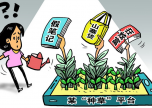在华东师大任教28年的数学教师周克希 翻译起文学经典也不含糊
我喜欢读杂书,这似乎是一个没什么出息的读书习惯。读杂书者,不爱长篇大论,看重杂文小品,不喜欢正襟危坐的说教,热衷启人心智的思想。故而,凡好读杂书者,往往不拘于某一领域,也不限于某种题材,只要感兴趣的,都会找来看看,也都能读到自己会心的东西。
作者 朱航满

我关注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并不是因为当时读过周先生的鸿篇译作,而是在书店里偶然翻到一本薄薄的杂文集《译边草》,内容都是讲述翻译心得的小品文字,很雅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经一位翻译界的前辈介绍,我认识了周先生,表达了自己对《译边草》的喜爱,先生随后寄给我一本新版的精装增订本《译边草》,并表示他的另一本随笔集也将问世,届时也会赠给我。
此时的周先生,已非我十余年前读他的那本薄本子时了,他因翻译法国经典文学名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而声名远播;他坚决拒绝使用已被读者熟知的译名《追忆逝水年华》,也引起了颇多争议。我读先生的一篇“译边偶拾”,其中谈到翻译之美,以为首先应该是精准,而他也把这个观念,归因于自己多年执教和研究数学,并由此深深领会了数学之美,乃是在于准确。先生在从事专业翻译工作之前,在复旦大学学习数学五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数学教职二十八年,翻译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但最终竟成为了他有所寄托的职业。这其中本该有颇多感慨和煎熬,可我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读到的不是遗憾、感伤,而更多是一种平静与温暖。
过去我有个偏见,认为好文笔都在作家圈子中。后来读书面渐宽,发现不少作家因为天赋,确实文笔了得,但优秀的翻译家,他们雕文琢句,汲取经典,几乎个个文笔上佳。周克希先生的文笔就让我分外喜爱,是典型的学者笔墨,文雅、简洁、内蕴深厚,于人在不动声色中有所收获,这是多年修炼的结果。有一篇文章,周先生谈翻译的过程,他把自己的译作比作刚刚诞生的小熊宝宝,“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由此认为虽然翻译很辛苦,但绞尽脑汁投入其中,“那种快乐,又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周克希先生的新作《草色遥看集》出版后,我果然收到了这本赠书。读了其中一些文章,我才知晓先生在业余钻研翻译之道时,非常注重向前辈和同行请教,他们向他传授了一个秘诀,便是在注重外文修炼之余,应多在中文上下功夫。诸如汝龙先生以《水浒》为佳,黄裳先生以为应多读《聊斋》,王辛笛先生推荐废名的作品,陈村先生则建议多读《史记》,还向他推荐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翻译家郝运先生,则建议每天多读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并表示他很喜欢李广田的小说和散文……由此想起我访问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时,他特别向我推荐了余光中的散文。看来优秀的翻译家,都有一位心仪的翻译对象,也有一位自己追慕的汉语作家。
也许受到这些师友的启发,周先生特别注重对汉语写作的大家作品的阅读与领悟,他特别喜爱沈从文、汪曾祺、孙犁、杨绛等现代作家,认为他们将白话文写作推向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这其中,他对汪曾祺的写作尤为推举,多次谈及,并认为汪的文字,清新、鲜活、有生命力,读后令人颇感余味尤在,仿佛“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而我注意到在一篇文章中,先生特别推举归有光的文章。这种对古文的喜爱,一种好处是文辞凝练,可学其“笔墨情趣”,更重要的是古人作文比较讲章法,这是作文的一个关键,今人在这一点上不太讲究和用心了。
我还特别注意到,周先生似乎对“草色遥看”一词颇为中意,这个词取自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由此记得我们结识之初,我知道先生好笔墨,常常练习书法,便冒昧求了一幅,以作纪念。先生将书作寄来,内容是李白的一首诗,钤的闲章,正是“草色遥看”。
(原标题:遥看周克希)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