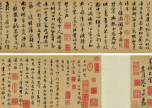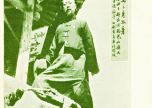2015年4月30日 中国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将于下月在京举行,引起我注意的不是那些待拍的宝贝儿,而是隐藏在那些宝贝后面的故事,比如隐藏在竹子后面的故事……

徐秉方 寒江独钓图留青臂搁

王新明 竹雕达摩
“为了让王新明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搞创作,王世襄特地在琉璃厂找了一块地方,但王新明没来……”
王世襄一辈子都在和收藏打交道,到了晚年,尽管收藏内容已经从古玩变成了现代艺术品,但他仍坚持古物研究收藏,尤其关心一些传统技艺的生存,特别是竹刻艺术。
范遥青,一介农民,对于竹刻非常痴迷。他与王世襄的相识颇为偶然。一次,香港著名收藏家叶义编印了一部《中国竹刻艺术》,范遥青便托人送去一件仕女臂搁,以求换此书。叶义收到这件臂搁之后眼前一亮,马上写信告诉王世襄自己的发现,拜托王世襄在内地打听一下臂搁的作者。王世襄辗转多地,终于在常州打听到范遥青,两人便开始用书信交流。在当时,范遥青的竹刻没有名气,不过作品却构思细腻、别具生趣,王世襄利用各种场合,极力向中外朋友举荐范遥青的作品。

薄云天留青秋林觅诗图臂搁

朱小华 留青虎啸图臂搁
元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曾提及南宋竹刻家詹成的竹刻:“雕刻精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在王世襄看来,范遥青的竹刻个性十足、风格经典,足以与詹成相提并论。
作为常州徐氏竹刻的继承人,徐素白先生的三子徐秉方也与王世襄交情很深。王世襄曾说道:“秉方先生幼承家学,专攻留青,四十以后艺大进,不独于见刀处现神采,要求在模糊朦胧不见刀处生变化。不然对此弥漫滃郁,满幅烟云,将不知如何措手矣。”
徐秉方擅长留青竹刻,在继承常州徐氏竹刻留青花鸟的题材之外,他开创了留青山水中云的新造型,柔美灵动。王世襄曾收藏了徐秉方所刻“启元白画山东臂搁”,与其他大家的作品一道被收录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
圆雕是竹刻当中最难的手法,在雍正乾隆时期的封氏兄弟之后,几乎没有几个擅长圆雕的竹刻家。因而王新明的出现,令王世襄倍感欣慰:“王新明深知‘文似看山不喜平’的道理,作品不寻常不落套,神奇怪诞,完全出乎人们意想,却使人觉得新奇。”
王新明为了生计经常参加各种展览会和评奖,商店出售的竹刻又不让署名,这让他的创作难免受到市场的影响,甚至还有商家利用他的作品冒充古代雕件上拍。王世襄在为王新明鸣不平的同时,也希望他能创作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宁可不卖也要在上面落款,如此才能成名成家。在王新明最困难的时候,王世襄花巨资购买并收藏了他的竹刻作品,一解他的燃眉之急。后来,为了让王新明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搞创作,王世襄特地在琉璃厂找了一块地方,但王新明没来,两人因此还闹了点不愉快。不过这件事并未影响两个人的交情,王世襄临终之时,将一包信件交给王新明,足见对他的器重。

1985年,王世襄先生观看徐秉方的作品。
相比于王新明,王世襄给予朱小华和薄云天的,则是更多的亲身指教与鼓励。
朱小华曾是河北雄县的一个普通农民,自学竹刻,因为看了王世襄的竹刻著作因而产生拜访他的想法。1997年7月2日,朱小华写了一封信寄到白塔寺东夹道乙21号,但这封信王世襄在两年之后才收到。时隔两年信还没有丢,两人的交往是奇迹也是缘分。
朱小华在与王世襄见面之初,对王世襄说自己在学习方絜的“陷地浅刻”法。那时,朱小华并未观摩古代竹刻实物,只是凭着书上的模糊图版就能对方絜的作品有所体悟,还能在作品当中显示出这个技法的一些特点,这让王世襄感到十分惊讶。
通过对朱小华作品的仔细研究,王世襄发现朱小华在“陷地浅刻”上颇有造诣,但也许是太熟悉的缘故,让朱小华在刻留青时很容易将“陷地浅刻”的刀法融入其中,使得作品变得拘谨。虽然“陷地浅刻”与留青法很难糅合,但王世襄却认为在一件作品中可以分开运用,“不妨某一部分用留青,而另一部分用‘陷地浅刻’”,这让朱小华茅塞顿开,在后来的作品当中不断实践,日臻成熟。
作为王世襄的学生,薄云天更是受到先生的引荐,屡次下江南遍访名师,学习竹刻技艺。薄云天的这个名字,是王世襄给起的,取“义薄云天”之意,大器而有力量。
2007年夏天,薄云天带了三件竹刻作品到王世襄家中请求指点。王世襄看后放到条案上,然后拿起条案下的一个纸箱对薄云天说:“这个纸箱,是专门用来盛你和朱小华竹刻作品的。”每次薄云天拜访,王世襄都会提前准备出好多有关竹刻的书籍和资料赠予,每次指点完竹刻之后,他都要加上几句话来鼓励他。
王世襄珍视年轻人对于竹刻的热爱。(张逸良)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