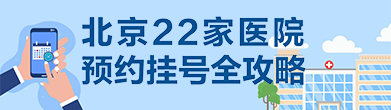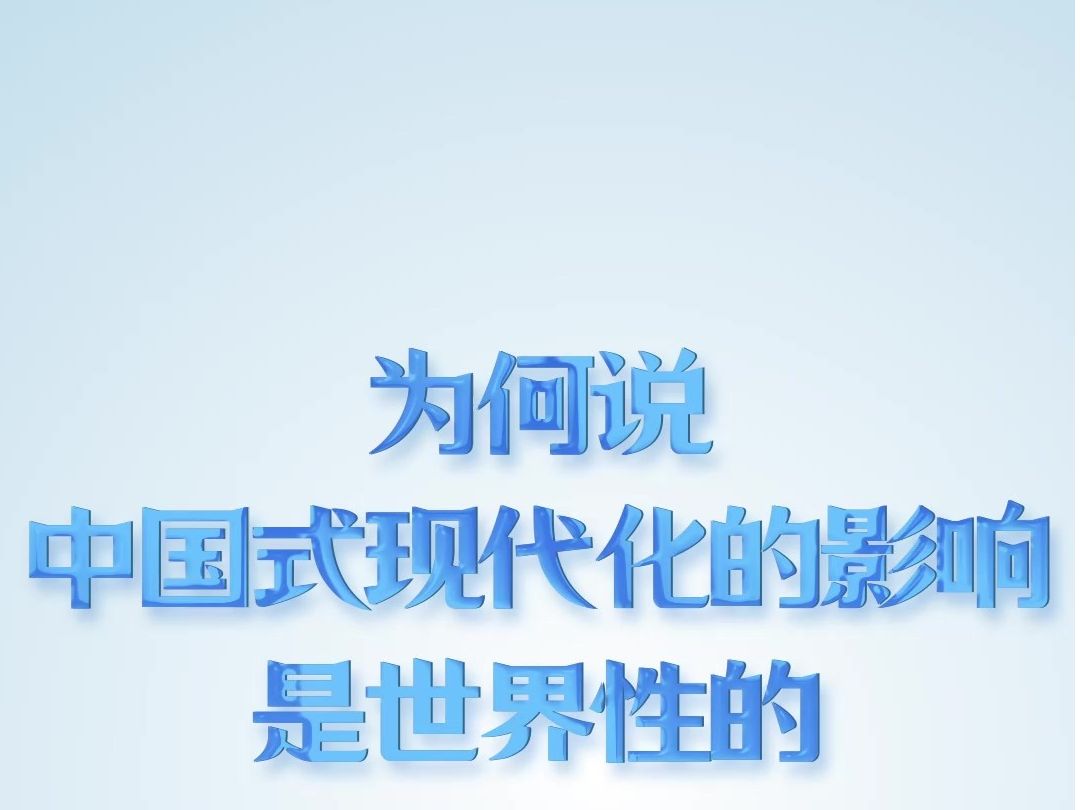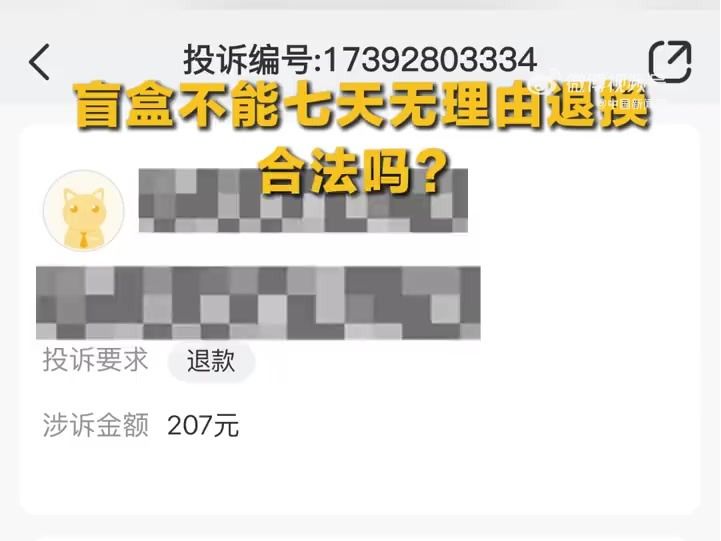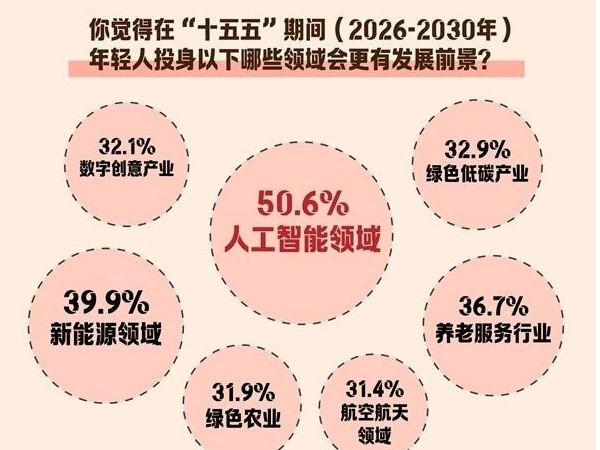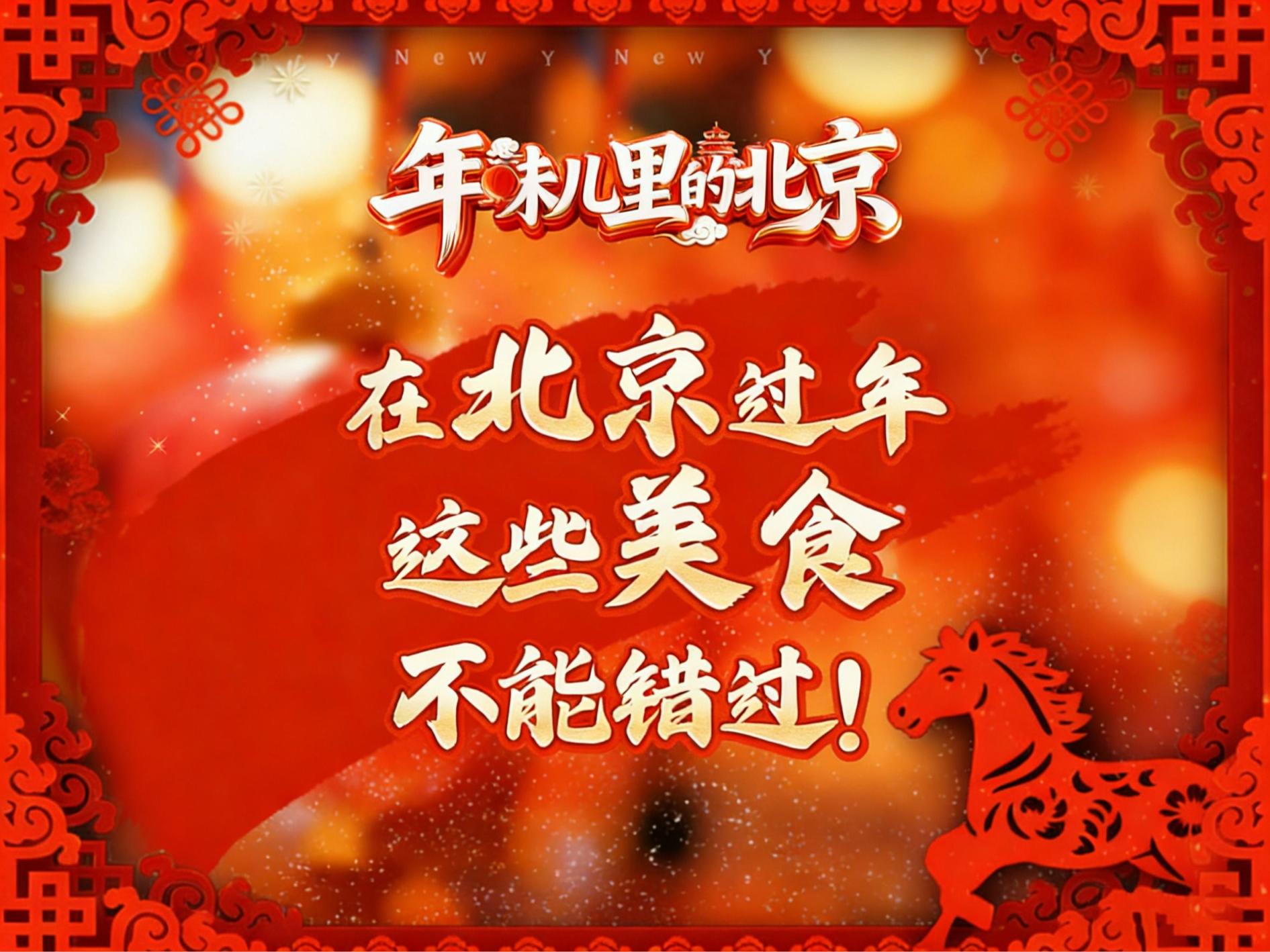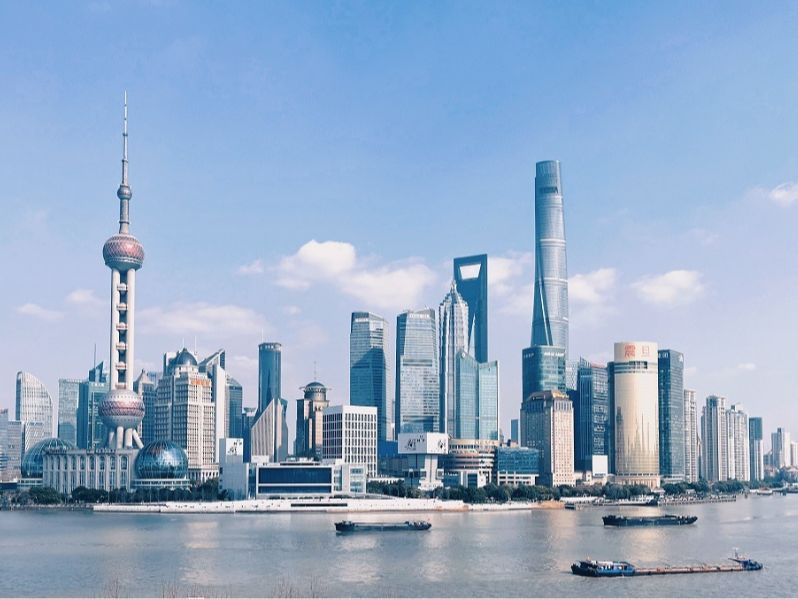-

57亿春节档:回望与思考
国家电影局2月24日发布数据,202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为57.52亿元,观影人次为1.20亿。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总场次超435万,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总场次纪录。与此同时...
新华社 -

应急车道多“急”能停?一文了解
近日,一位车主发帖称,自己返程期间在湖南境内高速公路遇到堵车,发现20多辆私家车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逐个拍照后全部举报到湖南高速交通服务便民平台。 不少网友对此点赞,称“...
国家应急广播 -

关于《国防动员法》,你可以了解这些
参考资料来源于:中国人大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更多热点速报、权威资讯、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来源:新华社移动端...
新华社移动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