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交道口南大街与府学胡同交会处,伫立着一座朱门灰瓦的古老建筑,如今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在老北京人的记忆深处,这里有着一个更具时代烙印的名字——“东四妇产医院”。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助产士的教室。

杨崇瑞留美时的照片。
时光倒流九十余年,这处院落前的景象更令人驻足:一对汉白玉麒麟镇守门前,身着整洁制服、步履匆匆的年轻女性,拎着特殊的“拜访箱”,箱内装着新式接生的器具,奔向京城的四面八方。这里,便是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原点——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而亲手点燃这盏生命之灯的,是一位终身未嫁,却被无数孩子视作母亲的传奇女性——杨崇瑞。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为产妇测量血压。
这座院落的选址本身便是一部新旧交替的京华烟云录。医院南侧的那条胡同,名为“麒麟碑胡同”。关于这条胡同,老北京流传着一段传说:明朝末年,一位名叫玲儿的公主因情伤离宫居住于此,她终身未嫁,却极爱孩童,凡经过府前的幼儿必抱来抚爱,久而久之,百姓视其为“送子娘娘”再世,便有了“麒麟送子”的佳话。
到清末民初,或许是沾了传说的光,这条胡同竟真的成了京城产婆的聚居地,胡同西边住着伺候皇家的御用产婆,巷尾住着民间接生婆。然而,传说终究护不住苍生,旧式产婆手中未消毒的剪刀和那一把把糊在脐带上的香灰,往往成为夺去新生儿性命的“无常”。

1929年,助产士随身携带的器具箱,里面医用器具等一应俱全。
1930年,杨崇瑞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新校址选定于此,买下被称为“公主府”的宅院和邻近民房。这选址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宣战”——她要在这个迷信与旧俗最深重的地方,用科学的双手夺过“麒麟送子”的接力棒。

1930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举办的宝宝大赛。
杨崇瑞这名字,今日或许不若她的学生林巧稚那般家喻户晓,但她却是林巧稚都要尊为“老师”的先行者。她生于通县的书香门第,自幼便有一股子倔劲,八岁时主动要求放足、解约、求学,一路读进协和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医学女博士。毕业后,她本可做一名待遇优厚的妇产科专家,但一次下乡调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妇产医院的二等病房。
1924年,杨崇瑞随兰安生博士深入河北农村时,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产妇因“产褥热”高烧不退,新生儿因“四六风”(破伤风)抽搐夭折,当地更有惨痛的俗语“只见娘肚大,不见儿走路”。面对高达千分之二百的婴儿死亡率,杨崇瑞意识到,仅仅坐在大医院里开刀,救不了中国妇女,只有走出象牙塔,去培训千千万万个懂得消毒和无菌操作的助产士,才能从根源上止住这淌血的伤口。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360名接生婆曾在这里受训。第一批30名学员,平均年龄54岁,图为结业时合影。
1929年,杨崇瑞辞去协和的高薪职位,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并在北平创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当她带着这所学校迁入麒麟碑胡同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听诊器和产钳,更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精神。她亲手拟定了八字校训:“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并将这八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校园一角。

刻着“牺牲精神 造福人群”的校训碑。
杨崇瑞对学生的要求近乎严苛,除了精湛的医术,她还要求毕业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在农村实习基地甚至要学会骑驴,因为在那些偏远的山区,只有助产士骑在驴背上颠簸的身影,才是产妇母子平安的希望。
在这座深宅大院里,身为校长的杨崇瑞没有一点架子。她常年穿着一件朴素的布旗袍,发辫盘在头顶,与学生轮流值班,一旦遇到危重产妇,无论风雨昼夜,随叫随到。有一年,一位贫困产妇在附设产院生下一名女婴后,因无力抚养想要遗弃,杨崇瑞不仅垫付了所有医药费,还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杨广仁,并一直供养她读到大学毕业。

妇产医院的免费病房。
抗战烽火曾一度打断了这里的宁静,幸亏杨崇瑞早在战前,便极具远见地将募捐来的款项兑换成外币,以“特款”形式存入国外银行。这笔钱,成了学校在乱世中维持生存的救命稻草。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初现,身在日内瓦,已担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的杨崇瑞,毫不犹豫地回到北京,出任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1929年,助产士携带器具箱上门出诊,到孕产妇家中访视。
在她的倡导下,构筑了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推广新法接生,短短几年间,婴儿死亡率骤降。尽管她一生未婚,但当人们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说:“我已经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杨崇瑞和本科第十班及实习班学生合影。
如今,那刻着“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碑早已在岁月中斑驳,但从“麒麟送子”的传说到现代医学的殿堂,杨崇瑞用她92载的人生,在京城的版图上,书写的那段传奇仍熠熠生辉。
来源:北京日报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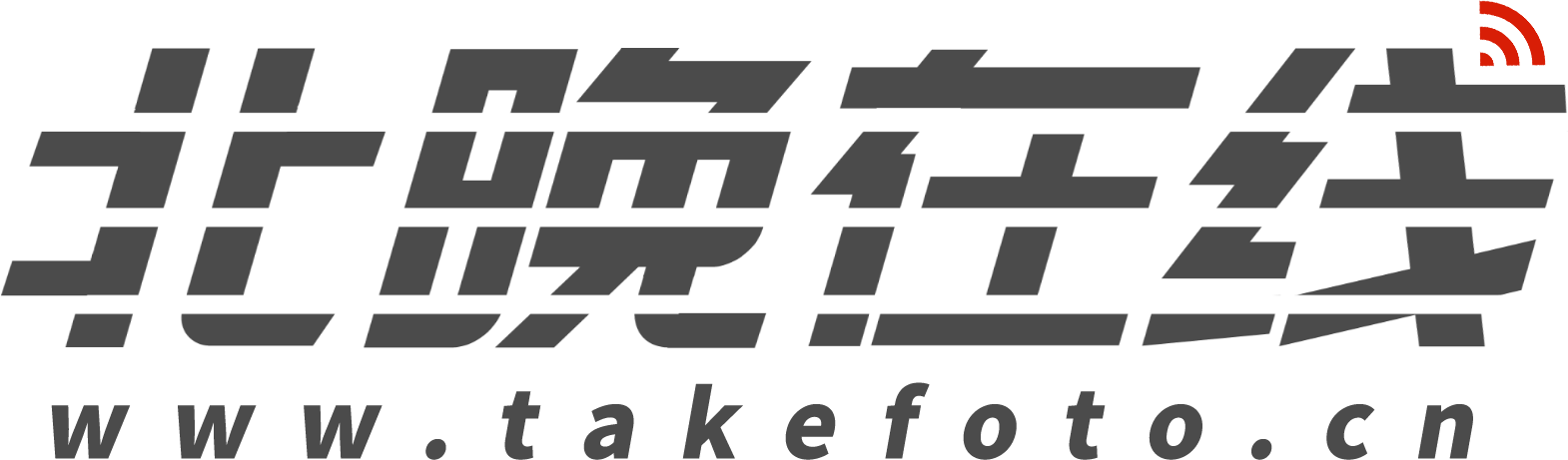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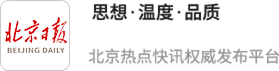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全部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