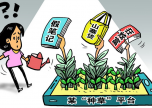据说黄永玉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卢浮宫里,他亲眼看见一对老年夫妇指着一张伦勃朗的老头像赞叹说:“啊,蒙娜丽莎!”这故事如今听起来,仿佛像个段子——时至21世纪的今日,蒙娜丽莎早已成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在艺术界“最熟悉的陌生人”,哪怕他(她)是对艺术最外行的门外汉。
作者:张玉瑶

人说去卢浮宫,乌泱乌泱的人群都是奔着三个女人去的:蒙娜丽莎、维纳斯和胜利女神。达芬奇笔下这个雍容典雅而稍显富态的贵妇,向着里三层外三层高举长枪短炮的人墙,永远不知疲惫似的展示着她那一抹似有还无的神秘微笑。
然而,问题又来了:虽认得蒙娜丽莎,但这幅画到底好在哪儿呢?在这个问题上,普通大众难免会有点卡壳了。毕竟多数人一进卢浮宫直奔蒙娜丽莎,并不是因为自己认为它画得好,而是因为“大家都说它画得好”。这个牢不可破的共同认知,来源于每个人道听途说而来的最浮光掠影的美术史知识。于是多数人怀着懵懂的预期,看了“真相”后也就散了,惟一的进步大概只是看到的女人的神秘微笑,从印刷品上转移到了对面墙上,从传说中转移到了可以泛泛纳进旅游见闻的有限个人艺术经验中。
“好在哪里?”在普罗大众的认知中,仿佛并不是该予以郑重考虑的问题——那是艺术家和艺术学者们的事。艺术学者们在学院里一本正经地严肃讨论蒙娜丽莎身后风景所运用的色彩透视,讨论这幅画作背后彰显的人文主义精神,年复一年出版一部部大部头的艺术史和艺术研究著作来予以重述和论证,但那些慢条斯理的高深专业“黑话”,却往往令大众昏昏欲睡。相比之下,大众更加好奇并乐于加以检验的或许是,蒙娜丽莎真的是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在对自己微笑吗?此二者或许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信息不对等和缺乏有效的交流渠道而已,但也必须意识到,这个不自觉的“二分法”,一方面显示出了艺术和大众固有的悬隔,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带有某种傲慢与偏见在里面。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普通人在温饱之余也开始拥有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艺术、渴慕拥抱精神升华的意愿时,这种不对等和渠道的缺乏,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阻碍他们的沟壑。长久以来,学院艺术和大众处于两条互不相交的轨道上,这虽根植于自艺术作品被经典化以来的漫长历史层积,但也难免有些令人遗憾。
因而这一两年中,当一些出自“艺术圈内人”的通俗化艺术解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市场和大众面前时,往往会受到不少关注、喜爱乃至追捧、“圈粉”,这其实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结果。这一类型的图书乍看起来小众,仿佛只是正统艺术史的“旁支”、“小道”而已,但认真数起来,竟也可以列出一个居然不算短的书单:《如何看一幅画》、《艺术原来可以这样看》、《胆小别看画》、《名画之谜》、《这幅画原来要看这里》、《这幅画还可以看这里》、《艺术小料》甚至日本著名动漫导演、宫崎骏的老搭档高畑勋也有个人观画心得《一幅画开启的世界》……当然,国内在这方面也并未落下,其中最有名者,当属“顾爷”的《小顾聊绘画》,擅长以谐谑的语言和网络化的表述来解析名画,大量抖搂艺术家们的段子和猛料,迅速收割大批粉丝,在闹哄哄、世俗化的微博上竟然能够以一名“艺术网红”的身份成功横空出世。
套用“科普”的说法,这些图书可以称得上是“艺普”,且同样印刷精美,不惜用大幅全彩来高清呈现画作原貌。从大的层面着眼,它们具备的是“架桥”的意义,即让经典艺术走入大众、大众有机会有渠道了解经典艺术。而从接受的层面看,这当然和文化趋向大众化、流行化的趋势,以及互联网所创造的“平的世界”有关,暗示出一种前代艺术学者未能多加注意却不可小觑的群众需求——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人们本质上是热爱艺术的,即便是和艺术最无关的人也并不会无缘无故排斥艺术,无论这“爱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自我丰富还是作为炫耀资本,其手段是研读学院派艺术史著作还是关注“艺术网红”们的更新。
笼统看来,“艺普”类型的书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虽然深浅程度有别,但作者都有艺术专业背景,又有较长时间从事普及工作的基础;其二,叙述方式通俗、生动、多样,深谙现代大众传媒传播规律,以“故事”代综述和观点;其三,不同于传统上各种以“入门”为后缀的简略版美术史,它们并不倾向于勾勒全景式的艺术史,而是倾向于将话题缩小再缩小,缩小到某一幅具体画中,手把手讲解“如何看一幅画”,不仅包括色彩、笔触,还包括一些特定意象的解析——也就是说,在纯美学的艺术范畴外,还有很大程度是“技术”的范畴。然而这对初入卢浮宫一脸蒙圈的艺术门外汉们来说,可能比讲述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艺术的演变传承更加地“有用”。
之于专业人士天生的敏感艺术触觉和通过长时间积累的深厚功底而言,“速成”自然不算是一个太好的词,但之于普通人而言,大抵也并不算坏。大多数人应当是怀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以并不多么正襟危坐的姿态翻开书的第一页,满心期待地迈入自己可以碰触和理解的那个艺术之宫中去。
跨次元的艺术大师

《小顾聊绘画》,给出了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进行艺术普及的一种范例。
作者网络通称“顾爷”,大名顾孟劼,是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设计师,在艺术领域是半路出家。“走红”缘于他以谐谑幽默的无厘头风格在自己的微博上发画家及名画背后的故事,无厘头在网络时代并不是新鲜的手段,但新鲜的是他瞄准的内容是向来被视为高冷的艺术领域,能够有效激发一波“反差萌”:众多几个世纪前故去的画坛大师,就跨次元地为21世纪的中国网民带来了平民化的欢乐。虽然“走红”是自媒体最为原生的诉求,但在此过程中,这些艺术家们是谁,他们做(画)了什么,这些基本的问题也能够随之得到科普。比如,为了说明印象派之父马奈在当时的地位,书中打比方说,“‘春晚’就好比官方沙龙,‘个人演唱会’就好比第一次印象派画展,那‘周杰伦’差不多就是马奈了……”,读者立马心领神会。
《小顾聊绘画》是以画家个体为结构的,即每一章讲一个画家。但画家的选择,据作者自己讲,却是非常随意的,全凭个人的喜好。已出的两本加起来,统共也不过十来位画家。如此,自然无法形成“艺术史”的勾连,加之每个画家个体的介绍也比较浅,因而其最直接的作用,大概就是让读者认识和粗粗了解了卡拉瓦乔、伦勃朗、莫奈、雷诺阿、梵高、塞尚等名垂美术史的几位重点画家及其特点。尤其考虑到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一些选择,截取的是一些相对更有趣、更有料的内容。以网络传播媒介及当下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而论,以上这些倒并非是作为其缺点而存在的,只是从接受层级来考量的话,它应当在艺术进阶的序列中属于非常入门级的读物,面对的是其自有的受众。或者说,其更大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多么丰厚的艺术盛飨,而是在于将众多吃瓜网友们聚拢过来,并尽量影响他们成为艺术的初级欣赏者——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装腔进阶法则:我有一个故事

如果说小顾属于“艺普”新秀,另一位作者中野京子就是此中大咖。这位在日本国内和国外都很受欢迎的艺术畅销书女作家、专栏作家,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方面有颇深的造诣。
中野京子在公众艺术普及方面十分勤勉,而且她的一系列作品如《胆小别看画》、《名画之谜》、《画框里的男人装》等,都称得上十分好看。然而这一种“好看”,和《小顾聊绘画》的“好看”是不一样的。中野京子用艺术吸引普通读者的方法,不是接地气的表述风格,而是艺术本身所深藏的幽玄与魅惑,以及她相当出色又悬念迭起的叙事笔法。
比如《胆小别看画》系列以“恐怖”为线索来解剖绘画,其中讲到了德加的名作《舞台上的舞女》,画中一个美丽而白皙、身着半透明舞衣的芭蕾舞者正在翩翩起舞,灯光明亮,色彩层次丰富,这个看起来如此美好高雅的情景,为什么会是“恐怖”的呢?会讲故事的中野京子接下来通过社会历史背景的叙述,以及结合画中各种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元素,令人信服地解析出这幅画是如何表现了当时舞女们的悲惨生活。又如在《名画之谜》中,她在比较分析提香、伦勃朗、克林姆特三位大师分别以裸女达娜厄(古希腊神话人物)为题创作的绘画时,从构图、光影、隐喻等多个方面解读了其各自所试图表达的意涵与情感,在那或含蓄或奔放的美之下,呈显现出三位大师各有千秋的风格。在这样的段落中,中野京子优雅而明朗的行文,又充分展现出了她在艺术鉴赏方面的专业性。
从画面的技巧赏析,延伸到更为复杂深层的社会历史因素,再充分发挥个人艺术积累和创造性联想,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探讨——显然,这样具有丰富层次的写作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也是专栏式写作与网络式写作的不同。中野京子从以上这些方面中又进一步提炼出了主题式的解读,关注恐惧、谜题、服装等等一个个浮现或隐藏在画面中的基本母题或共同情感,令解析的过程颇有悬疑小说意味。
这是一种剑走偏锋又十分抓人的艺术普及方式。比起具体的艺术史知识传授,中野京子所提供的更有效的启示或许正在这里,她很好地找到了一条艺术与大众之间交流沟通的恰当路径,不违背大众猎奇的心理,但也不因此将艺术拉下神坛,只是丰富了“美”原本单一的层次——它也可以具有世俗的为大众所观的那一面。总之,是停留于画面奇观也好,是向美的更深处探入也好,桥已经稳稳地架在这里了。
国内类似的“艺普”写作也有。从马赛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的董悠悠便将其在知乎网上的艺术专栏结集,出版了《被误诊的艺术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很有些中野京子式的影子。作者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女侦探”,将一幅幅具备“隐藏空间”的名画视作等待被解剖的谜题,只是其围绕的话题和风格用语更偏向网络化一些。和中野京子一样,好看是好看的,但二者缺点也同样明显:对于曲折故事性的“求奇”追求,或多或少会导致一些对于画作的偏向性选择,因而冠以“艺术史”之名,难免有些过大了。如何在充分表现“好看”以达到普及效果的同时,不喧宾夺主地遮掩艺术(视觉)之美本身的光芒,依然还是个需要平衡和解决的技术问题。
符号学的形式分析法

如何看一幅画?这幅画原来要看这里幅画还可以看这里。以上这些略显“简单粗暴”的指示,是几本书的标题。从名字里也可读取到,比起鉴赏来,这更像一部实操性读物。
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法国艺术史学者弗朗索瓦·芭布-高尔和日本美术史家宫下规久朗。两位学者一东一西,却不约而同选择从符号学的角度去传授看画的锦囊妙计。为什么不少光明伟丽的人物肖像甚至圣母耶稣像里,好端端地非要画一只我们觉得脏兮兮的硕大苍蝇趴在上面?为什么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一定要站在贝壳里?书、灯烛、梯子、镜子、面具等等都有什么隐含的意义?如此种种,撷取世界名画中常常出现的一些符号意象,大到太阳月亮,小到苍蝇蜘蛛,寻常到一蔬一果,以索隐的方式,阐释它们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沉淀下来的隐晦的意涵所指。
譬如,樱桃这枚“天国的果实”常常出现在宗教画中,以血红的颜色暗喻基督的受难,但同时也常常出现在世俗画中,源于其英文名cherry又有童贞之意,又暗含了性的意味。因此,画家们颇爱表现的主题是,让一个正处于美好华年、散发出浓郁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捧着一篮樱桃或一篮有樱桃的水果,看起来既纯洁又具有某种诱惑。稍有不同的是,弗朗索瓦的阐释更偏于宗教意味,毕竟基督教长期以来都是西方艺术史的总体纲领和表现对象,而宫下规久朗纳入了东方视角,以一个符号勾连起浓墨重彩的西方油画和清淡的东方水墨画,具有了某种比较的视野。比如青蛙,在日本以及中国常常很受欢迎,代表了一种讨喜的野趣,但在西方却是邪恶的象征,在德国画家马蒂亚斯的《死亡恋人》中,画得简直可以用毛骨悚然来形容。
然而,正如弗朗索瓦所言,“象征符号的意义常常会反转,就像手套一样。它们的双重含义仿佛硬币之两面:环境不同,一个物体表示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这些手把手教看画的“艺普”读物,无论是从符号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都只是给出了一种范例、一个最可能简单快速进入的入口,如果按图索骥,一一对应,难免陷入机械论,只见木不见林。毕竟,我们欣赏的是由各个元素所共同昭示出意义的整体的画,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一个个符号,后者只是辅助物。
技巧传授起来总是简单的,但美不是。正如故事讲起来总是直白生动的,但美不是。然而艺术的本质是美。艺术的欣赏是包括了理性和感性的综合性的体悟与理解,技巧和故事很好地铺垫了这一条普及之路,但也仅仅是普及之路,进入这扇门后的世界,还需更好把握。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