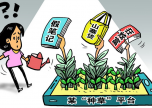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中关村笔记》入选“中国好书” 宁肯纪实作品记录中关村改革开放历史
“2017年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名单,北京作家宁肯创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关村笔记》荣列其中。
作者:成长
宁肯被读者熟悉的身份是一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等均在文坛引起不俗的反响。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却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此前完全陌生的科学家、企业家身上,为中关村——这一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最鲜明的名片写史作传。
在《中关村笔记》的前言中,宁肯这样形容写作这本书时的自己:“离开了熟悉的自己,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见各种各样的人,写从未写过的文字,几乎是另一个人了”。当写完后,“我已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
习惯了纯文学创作的宁肯为什么会挑战一部纪实作品?他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关村这一宏大的主题?这次非同寻常的写作之旅又对宁肯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北京出版集团的办公室内,与宁肯攀谈了起来。
中关村拥有完整的改革开放历史
记者:首先祝贺您的《中关村笔记》入选“2017年中国好书”,这本书与时代贴合很近,和您之前的创作还是差别挺大的,等于完全踏往了另外一个世界。您能先讲一下获得这个奖的感受吗?
宁肯:应该说还是非常振奋的,因为这个奖和其他奖不太一样,一是影响力比较大,这是大家公认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直接影响这本书的销量,让更多的读者读到。
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地方,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应该说,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和时代贴得比较近的作品,创作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候离你越近的东西越难写。因为大家感觉都差不多,你如何跳出题材的规定性,能够出新,能够找到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角度,或者你的功力能不能达到对这种热点话题有一个更深入的感受。
记者:起初是怎么会接受中关村这个题材的创作?
宁肯:我觉得属于一拍即合。我以前的创作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的概念,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有意识地要写一写北京。原来我觉得对北京的把握还不是太成熟,现在到一定年龄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能力,对北京的体验理解也更深入,所以准备以北京为题材,写一个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大概的想法。那么就要问,到底什么是北京?有一部分是我特熟悉的北京,我出生在北京,从小在琉璃厂的胡同里长大,对这一带的生活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老北京还不能涵盖整个北京,其实还有一个“新北京”。我们现在更多接触的是“新北京”,“新北京”的代表恐怕就是中关村,这是其他地方没法取代的,其他地方也有新的区域,但没有像中关村这么全面、有代表性。中关村包含了大学、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包括它拥有完整的改革开放历史,特别完整,自成体系。
这期间我写了一些作品给小说做准备,比如散文集《北京:城与年》,这时北京市有这样一个主题策划,要写写北京中关村,我本来自己也是想了解中关村,为我的小说做准备,但自己去联系人采访肯定会比较费劲,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欣然接受了。
我们这些年经历的最深刻的就是改革开放,但对我们作家来说,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也不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眼中的一段经济史,应该是在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中折射的一段历史。所以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一个擅长虚构创作的作家来写非虚构,我虽然写的是非虚构,但你仍然能感觉到书里有小说的特点。

记者:是的,我读这本书,感到跟吴晓波等作家写中国经济变迁的手法很不一样,您的切入点很细,写了许多大时代里人物的小细节。
宁肯:对,因为文学化的叙述有一个不可代替的功能,就是对生活的高度还原。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可以讲得非常清晰,逻辑也很深刻,但是它作用于人的理性、作用于人的思想。而文学会给你带到现场,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而对于表述历史来讲,也特别需要文学这种方式。所以我接到这项工作,觉得非常合适。
把文学里比较先锋的结构方式放在了书里
记者:这本书创作的过程,应该和之前小说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吧?
宁肯:非常不一样,首先需要阅读,熟悉资料。第二,要去现场采访,特别像你们记者,必须获得一手资料。小说有时候也有采访,但是次要的,观察和体验更重要。《中关村笔记》不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需要去进入别人的生活。另外,这本书写作的过程,思维方式,也是我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尽管写的时候已经很文学化、小说化了,但仍然有大量理性的存在。如何在这些采集来的素材基础之上,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建构,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您能选取《中关村笔记》中一些创作中特别花心思、比较困难的段落,讲讲您是如何处理的吗?
宁肯:开篇的冯康是我写的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数学家,特别是讲到数学的深奥理论,我觉得还是相当吃力的,一方面不能写得太专业,否则读者看不懂。另一方面你又不能出错,这其实挺难的。小说创作就不是这样,小说是相当自由的。所以在写《中关村笔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我不是我了,我怎么闯到这里面来了?有点分裂,好像从一个星球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时间长了以后真的会脱离开以前的样子,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也许会有不适应、失重、陌生的感觉,但有时候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也挺好。
比如写到新浪创始人王志东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他在弄中文之星,把微软的Windows进行汉化处理。还有像清华大学教授包杰,做量子频谱仪,他那种眼望星空的探索,真是“黑科技”的一种探索方式。像吴甘沙搞这种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包括程维这种资本的搏杀,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看他们的材料,也很惊心动魄。
但是在这样一种陌生化写作之中,我仍然保持了自己顽强的文学化创作。比如说选取人,以人为聚焦,以人带史。其次,写人也不是全面地写,抓住这个人最大的亮点、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把它集中聚焦,这是我这本书中塑造人物的特点。
我们再看《中关村笔记》的结构,书中有三位重要着墨的人物。一位是冯康。中关村如果没有数学、没有基础科学的底座,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把冯康作为一个贯穿的人物。与他平行的是柳传志。前者是做科学研究的,后者是中关村最有代表性的科技人员下海者。这两条线,整个骨架历史就搭起来了。中间是王选,其实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的。这三者之间,也写了许多人物,但篇幅都不是很长,点缀在他们之间,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手法,甚至是卡尔维诺的手法。我把文学里比较先锋的结构方式,运用到这本书里,这种结构的处理也仍然带有我作为小说家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段手记。别小看手记,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条珠的线,整个书的完整性是通过一段段手记给串联起来的。这种结构其实有点像科学,是吧?好像数学模型一样?所以虽然我是搞文学的,但在写作时无形中与科学也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本书能够获得“中国好书奖”,得到比较大的反响,可能都和这些手法有关。特别是在非虚构写作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写法非常新鲜,非常新颖。
记者:您为创作《中关村笔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素材收集,这些书中的人物会不会对您之后写小说产生影响,成为小说的角色原型?
宁肯:肯定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写了十来个人物,我就有一种写短篇小说集的感觉。写到他们的时候,有时候加工一下可能就会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如果作为长篇小说出现,我目前还真的难以预料是怎样的情景,但是肯定会出现,而且出现会非常重要。写这本书,为我增加了新北京的维度,老北京与新北京,合成了一个综合的背景。我觉得现在有条件去构思新的关于北京的小说了,如果我没有了解中关村,我就不敢去对它进行虚构创作,或者即使虚构了也会很薄弱的。有了《中关村笔记》的经历,我未来的小说里如果涉及到中关村的历史,我就会特别有底气。
(原标题:为中关村写史丰富了我的创作)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