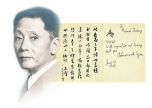2015年12月11日讯,在中国军事史上,蒋百里堪称“奇才”。他不曾指挥过一场战争,却料事如神是民国各路军阀争抢的军事高参;他一生以笔为枪,虽以兵学为专攻,同样长于政论、文史和书法,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相交颇深,被曹聚仁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出身贫苦之家,却深谙教育之道,四个女儿皆学有所成。三女蒋英是歌唱家,丈夫更是赫赫有名——我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钱学森。

1936年冬,西安归来在上海家中。
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1882年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寒微之家。翻开陶菊隐或曹聚仁二位先生为蒋百里所撰写的传记,很难不讶异于他的奇情奇才、文武一生。他传奇一世,令人津津乐道:在家乡时,被林徽因的祖父林颖赞之为“国家栋梁”;留学日本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和同期毕业的蔡锷、张孝准并称“中国三杰”;回国后,他一度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因校事多方受阻,一度曾以自杀请命;在学术上,梁启超为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他又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序;在军事上,面对日本侵略,他连续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公开发表近百次演说,宣称中国必胜,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大大鼓舞了沉浸在悲观情绪中的国人。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是他在其《国防论》扉页上的题词。然而遗憾的是,未能等到他所笃信的抗战胜利那天,这位文武双全的奇才就溘然长逝。1938年,蒋百里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享年仅57岁。数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迎来了和平年代,这位旧时代的军事专家也随之渐渐隐没不闻,蒋百里和他的作品一直只是军事等相关学术研究的对象。1971年,台湾出版了《蒋百里先生大全集》,而大陆若干年来,除了几本传记、选集和军事研究专著外,对蒋百里的资料还没有过全面整理,他在文史方面的才华与成就更罕能进入人们视野。
今年,历时十年编纂,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百里全集》终于面世。这套全集分为八册,约200万字,足足比台湾版多了100万字。文集的首发式特别选在浙江大学举办,蒋百里和这里有着不解之缘。1900年,18岁的他曾在求是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求学,传奇般的一生由此开始。横跨东西大洲,走遍全国各处,他平生四处奔走游历,而一个多世纪后,以这一套全集作见证,其清洁光荣的军人精神终于回归了故乡,回归了他的“浙江潮”。
这套《蒋百里全集》的问世,也了却了该书主编谭徐锋的心愿。这项浩繁的工作差不多花了他十年时间——最初在晚清众多飞扬激荡的仁人志士中注意到蒋百里时,他还是社科院一名二十出头的研究生,而如今等到这套书面世,他已经在出版行业工作多年,担任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的主编。在他看来,蒋百里身上有三种气质,一是文人士大夫的儒雅之气,一是军人的英武豪侠之气,一是浙江人特有的“硬气”。这三种气质交相辉映,将一个民国史上的独特形象推至人们面前,虽难以归类,却令人过目难忘。

蒋百里生前所用闲章
寻找蒋百里:一个人的十年修行
厚厚一套《蒋百里全集》,书做得很是精致。意大利进口条纹纸护封,里封布面精装,邀请著名设计师亲自操刀,看起来质感十足。然而编纂完成后,作为主编,谭徐锋并未感到彻底松一口气,反而“大大增加了对以往甘于寂寞、扎实做文献整理工作的前辈学者的崇敬之情,以及对这部全集的些微担心”。尽管,这套书从形式上来说,已算是“无可挑剔”的了。
谭徐锋是81年生人,在学界算是绝对的年轻人。2005年,和其他同学一样,还在社科院读研的谭徐锋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寻找着题目。现在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当时“野心很大”,“兴趣关注比较广,不是想着有个小题目赶紧毕业”。当时,最为流行的历史研究范式是对于某某人的“思想研究”,但谭徐锋觉得,“更充实”、“更丰富”、“更圆满”的历史,却是厘清某种思想是如何通过书写、演讲、报刊、仪式等诸种文本形式表现并传播开来,并以一种“挥发作用”对学界和普通公众产生影响的互动的过程。因此,学中国近代史的他将目光聚焦于清末革命动员之上,尤其关注起在日本活动的中国志士、留学生这个复杂群体。这个群体集结了彼时中国最为革命最具活力的分子,除了因难去国的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都位列其中。
面对比想象中更加汗牛充栋的资料,谭徐锋开始觉得自己“低估了这个题目的难度”。然而,正是在这个爬梳的过程中,一份名叫《浙江潮》杂志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浙江是沿海省份,文化发达,在日本的留学生为数不少,《浙江潮》就是由这部分浙籍留日学生创办的,为舆论宣传、鼓吹民主思想之用。而发起者之一,便是来自浙江海宁的蒋百里。海宁人杰地灵,文气纵横,王国维、徐志摩和后来的穆旦、金庸等都出自这里,沾染了故乡文气的蒋百里亦是如此。

蒋百里赋闲留影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这是蒋百里为《浙江潮》写的发刊词,登在该刊第一期上。文章血气沸腾,振聋发聩,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很“燃”,时隔这么多年,谭徐锋读来依然觉得“气势磅礴,让人心潮澎湃”。
那是1903年,蒋百里时年二十一岁,约莫如同现今的大二大三学生。《浙江潮》虽然出到次年的第12期就停刊了,但和同时期的其他一些革命刊物比,已经算是比较持久完善的了。它的影响力也波及甚广,比蒋百里长一岁的浙江同乡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在上面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包括著名的《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中国地质略论》等。这份杂志的影响传回国内,以至当时的浙江巡抚甚至还专门修书向远在日本的蒋百里垂询理政治军方略。

1936年,蒋百里与夫人左梅及女儿蒋英(右一)、蒋和(左一)参观德国柏林动物园
百年前的《浙江潮》将谭徐锋引向了蒋百里这个人,又将他引向了蒋后来更有名的作品如《国防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等。蒋是一个在各方面都相当有识见的人、极其丰富深邃的人,随着了解越深入,谭徐锋就越被其才情和品格所感染,反过来又更加激发他对其资料、踪迹的关注。但令人不甚满意的是,国内外既有的关于蒋百里的文献整理研究并不完善,内地解放后尚没有出过全集,而各种选集不仅遗漏了很多重要材料,甚至有以讹传讹的错误。譬如很多书会沿袭陶菊隐先生《蒋百里传》的说法,讲到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夺得了天皇赐刀,但谭徐锋觉得这个传闻颇有疑点,因为当时只有在陆军大学毕业时的第一名才有这个荣誉,而陆军士官学校是基层军官养成院校,毕业生是不可能获得天皇赐刀的。
因此,从那时起,谭徐锋开始发愿编纂一部蒋百里先生的大全集,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编就编了十年,如同现实版的日本电影《编舟记》一般。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编委会”或是“编辑团队”,所有的收集、整理、点校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前后参考了近百种资料。
“板凳要坐十年冷”,这个过程当然甘苦自知,但在查档案、找资料的过程中,又总有一些令他意外的惊喜。譬如他在南方的一个图书馆中找到一本《修学篇》,署名“诸暨蒋震方译”,和蒋百里本名蒋方震有些差异,且蒋百里非诸暨人。但巧的是,国学大师钱穆在读书时,因为学习好,老师曾将这本书奖给他。少年胡适也曾读过这本书,与蒋百里初次见面,就好奇地问蒋百里是不是他译的,蒋百里承认了,并在一篇不起眼的札记中提了这件趣事。“这才把这本书捋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旁证、自证就找不出来了。”说起这个收获,谭徐锋自是有一丝小小的得意,而去年《读书》杂志里面一篇文章提到《修学篇》时还语焉不详,根本未曾见过此书。比起早前台湾版的《蒋百里全集》,这部新的大陆全集足足多了一百万字,还入选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蒋百里狱中写经(局部)
和其他一些民国文人一样,蒋百里也曾有过许多笔名。单是一期《浙江潮》就有百余页,作为主编之一,蒋百里常常一人换着名字写四五篇,常用的笔名有飞生、余一等。谭徐锋将这些笔名仔细做了辨析,待为其找到确凿的根源,方才将文章收入全集中。其实,照他说,还有十来篇“没人认领”的文章虽没能收入其中,但咂摸来咂摸去,总觉得的确“很像”,无论是从笔法,还是从对于军事、音乐等方面的阐释,其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都像是出自蒋百里之手。在这些方面,无人能出其之右,但为谨慎起见,依然未予收入。
函札卷中,收入了不少蒋百里的家书。这其中,不少来自蒋百里的外孙、钱学森和蒋英的儿子钱永刚。钱永刚先生现在已有将近八十岁高龄,继承父亲的科学事业,从事计算机研究。他向谭徐锋提供的这些资料弥足珍贵。令谭徐锋难忘的还有一位海宁博物馆的吴德健先生,吴先生对蒋百里这位乡贤格外用心推崇,和谭徐锋打的电话加起来足有几百个小时。这些微小的细节都让谭徐锋深有感喟,八卷全集全部编完后,他提到,“工作看起来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我在档案馆敲出来、点校出来的,但背后其实有很多人的帮助”,他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线人”不下三十个,海内外都有。
现在做文献整理工作的人不多,照谭徐锋看来,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算学术成果,得不着什么钱,但若是材料万一没收集齐甚或点校、编辑出现失误,反而会被人诟病。但他庆幸自己是个“做事凭兴趣”的人,也不像学院派知识分子那样有什么压力,当初只是直觉感到“值得为这个人编这么一部书”。十年倏忽而往,他也越来越融入他的探索对象之中,这种参与者的身份难以割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经由你来发现的,隐隐约约有种脉络在里面。有生命的文献,就会像一块嶙峋奇石一样,能发出奇异的声响,在后面的历史中掷地有声”。

蒋百里全家福
蒋百里的“民国范儿”
“他是极度聪明、脑子很新的人。”谭徐锋这样评价蒋百里,并把他比作“现代诸葛亮”,——“能最大程度认识到蒋百里的价值的,大概是毛泽东了”。诚然,蒋百里一生没有亲自上战场带兵打仗过,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充当的是一个战略家而非战术家的角色。生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虽一生周旋于军阀之间,但蒋百里始终只在幕后,独立地提出建言,从不依附于谁。
“不光是坐而论道,也是起而行。”谭徐锋觉得,蒋百里身上真真正正体现了一种“民国范儿”他是一个“通人”,身上汇集着文人士大夫的儒雅之气,军人的英武豪杰之气和浙江人特有的“硬气”。这三种气质是相互交融的,方中带圆,柔中见刚,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以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军人的身份来规训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也以一个师长、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对待幼者、弱者。
“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蒋百里从小就是一个很硬气的人,十三岁时,母亲杨夫人大病一场,久治不愈。蒋百里模仿古人割骨疗亲的故事,偷偷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煎汤给母亲喝下。直到后来,母亲才发现儿子的伤口,与儿子抱头痛哭。
1912年,由袁世凯任命,从德国留洋回来的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上任第一天,他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对他们表明自己为国强兵的决心,并立誓道:“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做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在蒋百里的精心整顿下,保定军校面貌一新,学生们都很爱戴拥护这位新校长。然而,当时军界派别争斗严重,受段祺瑞政府领导的陆军部反对蒋百里的改革方案,明里暗里掣他的肘,干扰军校教学,令蒋百里极为气愤。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方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保定军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请假离校,潜回南方准备参加反袁。蒋百里劝阻学生说,天下大势还没有成熟,青年们学业还未成,不要着急出去,但也并没有起到效果。
6月18日,蒋百里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再次召集师生训话。他语调低沉,对学生们说道:“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我,我却对不起你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训话结束后,他让学生立正不动,自己则回到办公室,用手枪对准胸口自尽。幸运的是,子弹未能伤及心脏,蒋百里被医生救了回来,但这件事业已震动了全国。
蒋百里的“自戕以明责任”并非戏言,而是真的会去践诺,这是其自有的硬气与侠气,也是他作为军人的忠诚的天性,这一点或许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他自己对这一点相当看重,1917年时,还翻译了英国人斯迈尔的名著《职分论》(Duty),该书论证了人在社会上应恪守的职责。在军人观念和忠君报国观念之间,他调试那些可调试的,而不委曲于那些不可调试的。

《日本人》书影
“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蒋百里自戕后,当局请求日本驻华公使馆派最好的日本医生为蒋百里疗伤。与医生同来的,有一位女护士佐藤屋登。这次机缘,意外促成了一段美好的跨国姻缘。
佐藤不仅悉心照料蒋百里,还认真劝告他说:“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蒋百里听了深受震动,也从心底产生了对佐藤的钦敬与爱慕。
然而,当他向佐藤求婚时,佐藤却下不了决心,只好托词回到了日本家乡。蒋百里仍不死心,打听到了佐藤的家庭住址,接连不断地给她写信。佐藤回复说,一个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困难,劝他死了这条心。
蒋百里看见这封绝交信,急忙给佐藤又去了一封信,虽是表达爱情,口气中却带着军人那种不容驳回的命令意味:“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看到这封“硬气”的信,佐藤终于投降了。她把这这一封封炽热的信摆在父母面前,终于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佐藤离日前,曾这样祭告祖先:“佐藤已死去,其本人现为一中国妇人,因仰慕将军及热爱中国而嫁至蒋氏。”
佐藤回中国当天,蒋百里就和她举办了婚礼。婚后,蒋百里为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蒋佐梅。佐梅夫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嫁给一生研究日本的丈夫蒋百里后,如同一个她所允诺的“中国妇人”一般,不回日本,不说日语,不提身世,也未对女儿们实施日式教育。蒋百里去世后,她还亲赴前线,护理受伤中国士兵。除了长女早夭,两人其余的四个女儿后来也都各有所成,其中三女蒋英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一个普通日本女子,在中日作战的非常时期,顶着巨大压力嫁给一个中国军人,还能够一生践诺,情意弥笃,放下家国之思,着实不能不令人钦佩。蒋百里与佐梅夫人这对伉俪,在一个并不美丽的时代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国防论》书影
“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6年12月,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蒋百里飞抵西安,介入了“西安事变”的斡旋。在张学良力邀之下,蒋百里对同乡蒋介石进行了极有远见的开导,促使蒋介石逐渐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局势化险为夷。蒋百里并未依附某个党派,却为这个历史转捩点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蒋百里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亦是抗战时期。他一向致力于国防理论研究,相关讲学著述甚多。1937年,他把自己以前关于军事学的讲稿、著述汇集成《国防论》一书。书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军队在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连续丧失了大片土地。不少国民甚至精英知识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中,更有民族失败主义分子四处鼓吹认为中日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但蒋百里却以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日本通”的身份,在《大公报》上连载《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肯而深入地剖析了日本的历史地理、内政外交、精神性格等,指出其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认定其妄图用武力来分裂中国是徒劳的。一时间,《大公报》洛阳纸贵,出单行本后亦大为畅销。
斥罢日本必败,蒋百里又接连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等文章,宣明“中国必胜”。他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决心,不屈服,更是指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阐述了抗日持久战和运动战的基本雏形。
这一系列抗战文章的推出,在当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大大鼓舞了国人低迷已久的意志。虽然蒋百里当年11月即逝世,但他的思想精神却并未戛然而止,如今看来,依然因充满了令人感动的乐观志气以及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在黑暗中愈显光芒万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为他写了一副挽联道: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