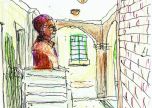2016年1月13日讯,从莫斯科乘火车三小时到达图拉时,遇上了大雨。同伴本来就对托尔斯泰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不感兴趣,这下脸色更阴冷了。我的想法是哪怕不去克里姆林宫,也不能错过亚斯纳亚·波良纳。通向庄园的路足足走了半小时。途中向一个女郎问路的时候,听说我们自己乘坐公共汽车找上门的,她蓝色的眼睛睁得溜圆,道:“好样的,好样的!”又指着来往的车辆,“看,都是私家车或出租车。俄国人也未必知道怎么乘公交车到这里呢。”

托尔斯泰
午后两点,我们终于来到了庄园附近。灰色的天空背景下,葱茏的树林清翠欲滴,浓得将周围的雾气都染绿了。或许太久没有见过这种包罗万象的绿,我有些怕似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然而眼睛率先被解放了,胸襟随即敞亮起来,嗓子直想唱歌!眼前的这片朴实乡村,才是真正的俄罗斯。
亚斯纳亚·波良纳是“明亮的林中空地”的意思,面积广阔,有一个大湖,幽深无边的森林,大片的苹果园,毫不婉约,完全是大大咧咧的风格,但是正和它质朴的主人匹配,有一股不受拘束的自由劲儿。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在这里,庄园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祖父爱赌大钱,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最后把自己的财产和妻子的陪嫁都挥霍光了,还欠了一大笔债,到了托尔斯泰父亲的时候,又把妻子的大部分陪嫁去还了这些债,只剩下亚斯纳亚·波良纳这一处庄园。因此,少年时的托尔斯泰生活得并不宽裕。成年后他不愁吃穿了,还是会为多花一分钱而不胜惶恐,这点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模一样。
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度过。八岁之前,他生长在这里,后来去莫斯科上学,升入喀山大学,不久辍学,去高加索服役,开始创作,写出童年三部曲。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从事教育和司法工作,写作《战争与和平》。35岁那年,他娶了18岁的索菲娅为妻。这位年轻的妻子很有艺术和写作的天赋,她崇拜丈夫,决定做他写作生涯的最好助手,为他誊写书稿,提出修改意见,翻译论文,参与托尔斯泰著作校订出版,履行“一个天才作家妻子的崇高使命”。托尔斯泰五十多岁时,举家迁往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住了十三年后,又回到出生的地方,直到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从亚斯纳亚·波良纳出走,11月7日病逝于途中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今天,偌大的庄园里,唯一“小”的处所,就是那座白色的故居房子。这是全世界托尔斯泰崇拜者的麦加。从外面看上去,这座两层的白房子跟普通的俄罗斯农舍没太大分别,一层有个凉亭,旁边种着几棵体格健壮的大树。
晚年的托尔斯泰一直为自己所过的生活而痛苦:“当我住在有15个房间的宅邸,享受着奴仆的侍候,我感到这种生活是可耻的。”到底是怎样的奢侈?遵照故居博物馆的要求,我们换上保护地板的拖鞋进去参观。里面大多数房间是狭小局促的。最大的一个房间是客厅,摆着一张长饭桌、一架钢琴、两圈沙发和几把椅子。想到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拜访文豪的人聚集的场景,你会担心四十平米是不是一个足够的面积。
卧室里的一切在1910年10月28日夜里托翁出走后就凝固了。床很窄,放有主人喜爱的绣花枕头,是做修女的妹妹绣的。床头小桌上摆着一个响铃,一座古老的圆形钟,一支蜡烛,火柴,还有几盒药。床头墙上挂着大女儿塔季扬娜的画像,屋子的一角放着洗脸盘,另一角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一瓶水,地板上有一架马鞍。墙上都挂着人像--托尔斯泰父亲的,穿一身军服;小女儿玛丽亚的,还有两幅是他夫人的,其中一幅很年轻,袅娜动人。床边有一个很大的桂冠,还有题词:赠与向生活的荒原大呼“我不能沉默”者。
书房的书桌上是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着蜡油的烛盘,一把圈椅、一副象棋、他的三张不同年龄时期的照片,以及翻开的书本都定格在一百年前的样子。它们和托尔斯泰夫人一样,不知道主人会一去不归。
如果说奢侈的话,只有钢琴沾点边,但别忘了托尔斯泰一家对音乐的热爱,这个乐器就像书籍一样必不可少。据他的友人、俄罗斯作家布宁回忆,托尔斯泰听音乐的时候常掉泪,正如当他听到谈到读到感动他的东西时他会落泪,音乐在他身上唤起的情绪随时可以从他激动的表情中看出来。
可就是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令托尔斯泰忍无可忍。他告诉玛丽亚:“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挨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却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
回到莫斯科,我又拜访了托尔斯泰一家在那里的故居。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索菲娅决定举家迁往莫斯科。这栋房子比亚斯纳亚·波良纳的白房子大多了,据说是从一个商人那里买下来的。
住宅一层是餐厅和卧室。托尔斯泰夫妇的卧室很小,两张单人床拼成一个大床,上面铺着索菲娅绣的羊毛毯子,床边摆一支欧式台灯,一道屏风将梳妆台和床隔开了。塔季扬娜的房间很特别,墙壁和桌布都是深红色调,一望便知主人的热情爽朗。墙上挂着她的肖像,极富魅力,是列宾所画。列宾是托尔斯泰一家的好朋友,他创作了好几幅托尔斯泰的肖像画,其中一幅很著名是“耕田的托尔斯泰”,收藏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塔季扬娜喜欢绘画,在会客厅一角挂着她的油画作品。房间中央,几把椅子围着一个精巧的圆桌,是塔季扬娜和朋友们聊天喝茶的地方。桌布上面密密麻麻的签名显示了它的不一般,签名者均是当时俄国知名的文化人艺术家,塔季扬娜突发奇想,索要了他们的签名笔迹,后来亲自动手描绣下来。玛丽亚的房间就简朴多了,床、柜子和桌椅都不加修饰。她性格文静恬淡,一心跟随父亲办教育,教农民的孩子念书,是父亲最知心的朋友,可惜去世很早。
其他孩子的房间简单明快,各种生活用具一应俱全,这是他们心思缜密的母亲布置的。这层还有间教室,索菲娅在此给孩子们授德语课。除去夭折的婴儿,托尔斯泰夫妇共养育了十三个子女,生养的责任全部压在索菲娅一个人身上,托尔斯泰的产业管理也要她来操持,若非具备不可多得的管理才干,是做不来这些的。在二层,有个小会客厅,就是整栋房子最缤纷的一间,其中一张靠窗的小桌子便是索菲娅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她在此起草文件,和别人商谈出版合同,总之,她要让丈夫不被任何琐事干扰。索菲娅每天忙得像赴死一样,其日常生活情景如她所描述:“人们说,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在死前总是很操心。廖瓦契卡(指托尔斯泰)整个冬天都是感情冲动地,含着眼泪激动地写作。我是如此的操心,如此的急急忙忙,觉得事情是如此之多。”
二层的大客厅约有70平米,钢琴靠在门边,脚座踏在一张熊皮上面,这是1852年托尔斯泰狩猎时的战利品。餐桌很大,可以围坐二十几人,沙发座椅也很多,可以想见当年高朋满座的画面。布宁回忆他和托尔斯泰第一次见面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似的白胡子老汉,穿一件像袋子一样宽大的灰棉绒布上衣,迈着有点罗圈的双腿走来,他摊开手掌,一把抓住我的整个手,轻轻捏了捏,亲切中含着一丝忧伤,甚至是悲悯。我发现那双灰蓝色的小眼睛根本不可怕也不锐利,只是像野兽一样机警。”告别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他说:“生活中本无幸福,只有幸福的闪光,要抓住它。”
但托尔斯泰后来放弃了这些抓在手中的“幸福的闪光”。他对莫斯科的伪善生活厌烦透了,尽管在这里他也可以饶有兴致地做鞋子,但和乡下生活是两回事。他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奢侈的生活,但是依然不能让他满足,最后,他离开亚斯纳亚·波良纳,将自己彻底放逐。
晚年托翁三次从庄园走出
进入老年后,他曾经无数次打算出走,他想挨门乞讨,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只为那“自由的狂喜”。
1884年是第一次,但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感到自己缺乏力量了--他不得不回到家里,回到妻子身边,妻子正在临产,当天晚上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13年以后,1897年,他第二次出走。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封信,充分阐述了自己出走的原因:“我决定逃走,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而且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孤独,其次,孩子们现在成长起来了,而我在家中的存在不再必要……印度人快满六十岁时就离开家庭到森林中去,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晚年都想一心一意地侍奉上帝,而不再去嬉闹、搬弄是非,或是打网球,我也一样。我就要满七十岁了,一心渴望安宁、独处、和谐 --即使是不彻底的成功,也不愿再与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知如此惊人的不一致。”果然没有“彻底成功”。因为抛下家庭就意味着只顾自己,而这样对家庭,对妻子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又是一个13年。1910年10月27日深夜,索菲娅悄悄走进丈夫的书房,寻找丈夫留下来的遗嘱。这让托尔斯泰决定第三次出走。他在28日的日记记录道:“不知道为什么,这引起我无法抑制的憎恶和愤怒。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约一个钟头。索菲娅开门进来,问我身体怎样,憎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起来。我数了数脉搏,97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
临走前,他将一封信交给小女儿,让她转交给妻子。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请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家里的处境正变得、或者说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除了其他种种原因,我不能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的奢侈的环境里。我现在所做的,是在我这个岁数的老年人通常所做的--离开尘世生活,在孤独、宁静中度过余生……”
究竟无法忍受什么?
他和夫人多年来为了朋友切尔特科夫,为了财产不停地争吵,已经到了使他无法忍受的地步。切尔特科夫是个狂热的托尔斯泰信徒,他控制欲极强,常常严厉地责备托尔斯泰口是心非,不肯放弃全部著作的版权和收入……这令托尔斯泰夫人非常愤怒,“切尔特科夫从我这里夺走了丈夫的心和爱,还要从孩子和孙子嘴里夺走面包。”索菲娅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小说家通过脑力劳动获得报酬和地位有什么可耻,为全家人着想,她坚决反对放弃托尔斯泰的版权。两边都在对托尔斯泰施压,“我在这疯人院里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辞世与归乡
跟他一起离开的医生回忆了离开亚斯纳亚·波良纳后的情景。马车走向莫斯科往库尔斯克方向的铁路小站谢基诺,到站后他们上了一辆从图拉开往奥廖尔的车,到了戈尔巴乔沃换乘,下午抵达科泽里斯科。他在那里停留下来,在那里给小女儿写信。第二天小女儿就来了,说托尔斯泰夫人知道他出走后曾经两次企图自杀,整天嚎啕大哭,有时用小锤刀子剪刀扎自己。她还带来母亲写的一封信,也疯狂得吓人,让托尔斯泰心惊胆战,他不能停留,只能继续向前走。10月31日,一行人到达阿斯塔波沃。托尔斯泰病情加重,他意识到即将进入生命的最后几天。看着别人为他忙碌,他又难过起来:“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们却只想到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11月1日,他给长子长女写遗嘱。6日,莫斯科的医生到。在托尔斯泰弥留之际,索菲娅赶到了,但被拒绝与他相见,最终她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没了呼吸。7日凌晨,托尔斯泰悄然辞世。
托尔斯泰下葬以后,白房子就开始像博物馆了。托尔斯泰夫人说:“三天以后这屋子就像死了一样……都要走……”他的出走实际上不但让自己破产,也使整个家族破产。托尔斯泰在遗嘱中将著作版权交给了赞同他主张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而不是妻子,他甚至还口授了另一个遗嘱:“最好从你妈妈和哥哥手中将亚斯纳亚·波良纳买下来分给农民。”几年后,亚历山德拉果然将哥哥的土地买过来分给了农民。十月革命后,托尔斯泰的著作权被“收归国有”,他的后人漂向世界各地。他的次子伊利亚后来在美国病死,知情人说他差不多是穷死的。
托尔斯泰被安葬在庄园,长眠于幽静的绿荫丛中。按照他的遗嘱,这块墓地没有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十字架。我从白房子里出来,已经快到四点了。当天还要赶回莫斯科,时间有些紧迫,但还是不想放弃寻找坟墓。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怎么走,我记了个大概,向她指的方向连走带跑过去。
跑了有一公里的样子,气喘吁吁,还是没找到坟墓。前面有几条小路,周围没有一个人,只有小松鼠跳来跳去。我向雾蒙蒙的树林深处望去,希望能和托尔斯泰洞悉一切秘密的目光相遇。周围那么安宁,雨声沙沙,草木芬芳,如童话世界。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我停住了脚步。托尔斯泰埋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他不希望被打扰,就像我现在不愿意被任何人、任何事情打扰一样,只想专注地感受每一点每一滴流逝的时光。
据朋友们回忆,索菲娅最后几年瘦了,体弱而少言语。但她每天都要走一俄里路去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夏秋两季她每天都带着鲜花去上坟,在那里的一张长凳上久坐,陷入回忆。
不少人谴责索菲娅,认为是她逼走了托尔斯泰。她不能理解他,有时会歇斯底里大发作,与他对着干。他想过简朴的生活,她认为是自虐,他倡导禁欲,她就讽刺“那你为什么要结婚,还生了这么多孩子呢?”。当他把所有财产、包括大量的农民转到妻子的手中时,她却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农民的处境比原来还要糟糕了,这让攻击托尔斯泰的敌人迅速抓到把柄。
他们也曾幸福过,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吉媞。 “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像我这样幸福。”索菲娅说,她有一种奇特的广博无垠的感觉,这正是与另外一个人融合的真实感受。两人初识的时候索菲娅年仅12岁,刚刚退役的托尔斯泰则小有名气,对于这个童年挚友的女儿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再次相逢,索菲娅已长成婷婷少女,令托尔斯泰十分钟情。托尔斯泰求爱的过程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求婚的现实版本,当时他用一点铅粉在桌子上撒出了他不敢启齿的词的第一个字母,索菲娅毫不费力地猜出他要说的话:“您的青春和对幸福的需求十分清楚地提醒我,我已经老了,不可能得到幸福。”托尔斯泰震惊了,他认定与自己共度终生的那位姑娘只可能是她。
要使托尔斯泰幸福可没那么容易,他非常善变,念头飘忽不定。孩子病重,妻子分娩,都不能让托尔斯泰受干扰,即便如此,索菲娅还在手足无措地检讨:“是我的过错,直到今天还不知道丈夫喜欢什么,不能忍受什么。”诗人费定说过:“索菲娅是在刀刃上走路”,托尔斯泰最后的诀别信则将刀子彻底扎进她心里。而就在三个月之前,他还声泪俱下地对她说:“我觉得,没有你,我简直无法活下去。”
托尔斯泰过世后,有人去拜访索菲娅。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满面倦容,但是从容大方,说话的时候不笑,也不提高嗓门。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说了下面的话:“我和他生活了48年,也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但临终之时仍然对孩子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忠实的妻子。”
托尔斯泰到底有多复杂?他用人类精神中一切最精致最丰富的东西充实着自己,也把最矛盾冲突的东西集中在自己身上。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是什么?理性对这些心灵的问题不作任何解答,只有意识深处的某种感觉在解答。自从有人类以来,他们解答这个问题不是用语言即理性的工具,不分生命的表象,而是用整个生命。”
站在树林里,我望向外面的天空,已经比刚来时晴朗了。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真。在生活中也好,艺术中也好,只需要做到一点:不说谎。”这样一个用全部生命来追求真我的人,告诉自己“要时刻准备死,学习更好地死”的人,还会继续感动着世界上向生活的荒原大呼“我不能沉默”的人。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