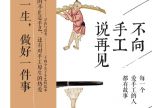今天咱们讲讲这个修眼镜的北京师傅的故事。
刘宝祥的小店,位于潘家园国际眼镜城10层。一间约有20平方米的屋子,柜台外面摆着沙发、眼镜架展示柜,柜台里面则是维修桌和一些设备。
工具不一而足,大到激光焊接机器,小到一颗螺丝一个弹簧。
他维修的手艺有多好,我不懂,我想大家也不太懂。只说一样吧:我们常用尖嘴钳子,这钳子,口粗口细,多少有些区别。我们日常家用,有两三把足够应付。
然而他的维修桌旁边,挂着一排尖嘴钳子。数了一下,20多把。

刘宝祥在忙碌着。
刘宝祥戴着个棒球帽,身着T恤,坐在柜台里面跟个眼镜较劲呢。他今年55岁,很瘦,看起来干练、利落。
正在修理的眼镜,是个德国产的无框镜架,两个镜片连接处本应和鼻夹相连,但断开了。他在显微镜下,以激光焊接进行修复。
不一会儿客人来了,看到焊接得牢固而隐蔽,很是满意。留下200块钱。下午不到两个小时,进进出出几位客人,刘宝祥的收入大概有四五百块钱。

刘宝祥在焊眼镜。这机器看起来够高科技的。
这个小店每个月租金3000元。不成问题,并且每周五刘宝祥固定给自己放一天假。活嘛,总是干不完的,赶上好修的,一天忙忙碌碌修它十多个;赶上麻烦的,一天未必能修好,而这工夫也不一定能值很多钱。总体来说,“比起上班是好多了。”
“但修理眼镜其实没有手工制作眼镜挣钱多。”
刘宝祥说着,从桌子下面拎出一大贯眼镜材料,“我在北京眼镜厂当了二十多年技术员。我最喜欢的就是给客人制作手工的眼镜,那些作品上不仅有我的手艺,还有我的美感。”

这些花花绿绿的材质,通过刘宝祥的手,都可以变成眼镜框。
那么,为什么您还要每天为修理眼镜忙活呢?
因为,“每个来到这儿修眼镜的人,一定都有他自己的原因。”
比如本文开头那一幕。
北京眼镜厂,诞生于1956年公私合营,一些眼镜行业手工业者组成工厂。小时候,我身边爷爷奶奶等老人戴的眼镜,都是“京字牌”,便是北京眼镜厂的品牌。

眼镜腿上三个字,便是“京字牌”。这是前些年我在旧货市场买到的,很便宜。
刘宝祥生于1961年。18岁高中毕业,那是在1979年,他来到北京眼镜厂工作,也就是今天眼镜城那块地方。
刘宝祥说,当时北京有很多眼镜厂,均为一轻局下属,他所在的北京眼镜厂当属龙头。
比较著名的还有608厂,也就是今天幸福大街、新京报的那块地方。

幸福大街上,北京608厂。来自街景地图。
当时这些工厂大致有个分工,北京眼镜厂以生产镜架为主,而608厂是军工厂,有玻璃仪器生产条件,因此承担更多镜片生产的任务。后来608厂与美国博士伦合作,生产了隐形眼镜。
刘宝祥的母亲也是北京眼镜厂的老工人。接班,这是那个年代全社会的同龄人几乎都经历的过程,但刘宝祥不太一样。
并非因为他的身家有什么特殊,仅仅是因为——
“我从小,手碎。”
北京话管这个叫“闲零”。他家里的半导体,自行车便会被他拆掉。
爱动手的人,都有个琢磨劲儿。因为拆了之后,你得想办法装上,否则得挨揍。
此外,“找块不锈钢便能抠个啤酒启子,有块铁板便要拍个簸箕。”看来年轻时候手艺不错嘛。
恰逢1980年刚刚改革开放,北京眼镜厂与香港开始合作,由香港提供技术、设备,生产新技术的“铣形架”。大致意思是,有机材料以机器削磨雕刻,把整料“抠”成镜架。这种镜架产品,在眼镜行业打破了二十年一贯制的传统镜架,后来“卖疯了”。

老眼镜架,京字牌。不过我也不懂这应该算是什么技术生产的。这种眼镜架是八九十年代最常见的。
刘宝祥解释,最初是金属镜架,后来咱们用的眼镜架大都通过类似膨胀的技术生产。接着铣形架成为主流技术,因为铸造技术达不到要求。现在则大都是铸造了,成本更低。
流水线式生产中,每个工人其实真的就像一颗螺丝钉,虽然不能少一颗,但是,换一颗,一样能用。
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北京工人乃至中国工人来说,这便是后来他们下岗的原因之一。当然,并非主要原因,只怪那个体制,走到了尽头。
而刘宝祥并不说自己“勤于动脑,勤于动手”而只是说“手碎”,看来当时,他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手艺,后来能在下岗大潮之后,站住眼镜一方阵地。

刘宝祥的一大排尖嘴钳子。
“我就在厂里各个车间转悠,看那生产过程。嘿,发现这儿有个技术问题,一帮人正在商量呢,我也赶紧往前凑。琢磨来琢磨去,拆拆装装,居然捣鼓好了。”
这个时候,“再一抬头,车间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自己往外走,边走边想,“这本来也不是我的活儿啊,怎么最后就剩下我在干了呢?”
没有白流的汗水。这么折腾了几年,刘宝祥还真成了个技术小能手。再不用他自己去串,因为各车间班组有点儿问题,都会主动来找他。
工作中互相帮助这是应该的,他和别的“二级工”一样,每个月38块钱工资。
这种状态持续到1990年。
那一年,日本的一家公司“佐佐木”,来与北京眼镜厂进行合资。厂里1000多人,选派10个人去日本的工厂学习技术,这个机会落到了刘宝祥头上。
“高兴,真高兴。当年我孩子三岁,可我还是去日本呆了整整一年。”

这是1994年1月,北京晚报刊登的大明眼镜的广告。“佐佐木”、“野尻”两个品牌为主打产品。
这次出国,让他大开眼界。“感觉日本人对我们没有什么保留。”国内的眼镜生产其实已有很多年,“虽然知道眼镜应该怎么做,做出来也挺像样,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在日本,他和同事们有机会相对系统地,了解了眼镜设计的一些理论,大概包括今天我们常说的美学、人体工程学等。
“比国内强多了。他们根据全世界不同人种,都有不同的设计。各种材质也都有相关的理论。”
就在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们,为假冒伪劣商品、售后服务而苦恼的时候,刘宝祥已经明白,“做事应该科学、严谨。”
做事科学、严谨,这不是废话吗?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编辑部的故事》里面,傅彪客串的那集,有句台词儿,“谁家没砸在手里几件儿电器啊。”

《编辑部的故事》第13集。产品质量问题困扰我们生活,其实这一集里,傅彪扮演的读者来向编辑部反映的,正是日本音响的质量问题。刘书友听了,悄悄问牛大姐,“这日本人现在也不好好干了?”可见当时大家心目中,日本产品算是好东西。
我们还在用“发展太快因此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理论,聊以自慰的时候,人家日本已经在扎扎实实做事儿了。
也难怪那年头,中国人喜欢日本电器。
这次中日合资,又是非常成功。除了和佐佐木合作的北京眼镜厂,还有和日本野尻公司合作的上海眼镜厂。
两个厂的产品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以致于市场流传,“南有野尻,北有佐佐木”。又因为两个厂设计有所差别,还有传言叫“男款有野尻,女款佐佐木”。
而刘宝祥的个人档案关系,也从此落到了这家合资厂。他算是技术主管人员,几乎参与每一个镜架的设计、定型等问题。

这些积累,都是今天刘宝祥手艺的来源。
也正是因为稍微脱离了传统工厂的体制,“1990年,我的工资拿到了380块钱。”
干到了1996年前后,北京的市场仍然不错,但是,日方那边发生了变故。“日本当时经济状态不好,而且公司创办人佐佐木老人年岁大了,听说家里也没人接班。他的公司,被另一家名叫‘青山’的公司收购了。”
北京这边的合作关系,也被新公司继承。在刘宝祥看来,过程挺顺利,而且,他第二次拿到了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这两年,我算是把眼镜生产,系统地好好学了一遍。”
终生受益。
按照1990年北京眼镜厂与日方的合同,双方合作15年。至2005年期满,双方已经有了一些矛盾纠纷,不再继续合作。
与此同时,南方的厂家兴起,北京眼镜厂这样的传统工厂早已被冲击。
也就是说,刘宝祥下岗了。他想起以前国有体制的好处,但是回去一看——
“眼镜厂比我们惨多了,早就停产了。”
好在自己有技术,不愁没饭吃。南方的不少工厂来聘请专业技师,他应邀受聘,以每月7000元工资,前往深圳的一家工厂做技术管理人员。

刘宝祥的修理桌。
但他接受不了那个环境。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场景——
老板说了啊,大家交流要说普通话,不能说广东话。要照顾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听得懂。
坚持了几天,人家还是喜欢说方言。于是大家一起开会,刘宝祥坐在人群中听天书。
不一会儿到他发言了,他也说了一些看法,可是,“我琢磨,估计我说的那些话,之前他们已经讨论过了。”
人家表面上对你很尊重。“老板说了,每三个月我能回一次家,飞机来回给报销。在单位,我吃小灶。”
但对于刘宝祥这种不想混日子的人来说,生活上的优待,改变不了事业上的失落感——
“在北京佐佐木的时候,每个产品都有我的参与,有我的心血。让我觉得我是企业的主人。”而在这里,似乎企业与他关系并不大。
于是,“与其说广东话,你们还不如说日语呢。好歹我在日本呆过两年,日语还能听懂一些。广东话完全听不懂。”
半年之后,他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但是刘宝祥不愿意自己开店,“思想还是有误区……感觉个体户都不是好人。”
但他已经在眼镜行业中干了二十多年,甚至可以说相当成功。

刘宝祥的尖嘴钳子们。
所以他认为,自己对眼镜行业的情节一直都在。
“你啊,还是不能离开眼镜。”给他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他的师父、北京眼镜厂的老技师刘嘉琪先生。
刘宝祥说,现在年过七旬的刘嘉琪老师傅,也在眼镜城里从事修理等工作。据说老先生手艺非凡,为国内的影视剧组定制过无数的眼镜道具。

现在的潘家园眼镜城。来自街景地图。
后来刘宝祥才明白,师父之所以给他这样的建议,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师父至眼镜厂停产、下岗,始终没有离开老工厂。直到下岗后,潘家园地区形成“眼镜村”,师父也在这里摸爬滚打,凭借自己的手艺和匠心,取得一片天地。
2008年4月,刘宝祥的小店,或者说修理铺或者说是作坊,终于开业了。“我拿着一把锉,一个钳子,就上班去了。”

各种工具。
第一笔买卖,是个修眼镜的焊接工作。刘宝祥挺顺利,按照顾客要求修好了。
“顾客接过眼镜的第一句话:真棒哎!”
一句久违的赞赏,让刘宝祥备受鼓励。
接着顾客问他,“多少钱?”
他懵了。“就这点儿手艺,还能挣钱?想当初我在工厂里,给人家修了数不清的眼镜,哪要过钱啊。一根儿烟就足够了。”
这些老故事,刘宝祥讲得津津有味儿。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应该转变观念了。于是,第一笔生意以50块钱成交。
50块钱变成了新的工具,新的工具让他更好的修理眼镜。良性循环很快就开始了。
前面说过,刘宝祥的小店,在眼镜城的10层。一般情况下,买眼镜修眼镜的人,主要都是在楼下溜达,很少有人走到这里。
“所以,如果他们爬上10楼找到了我,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许他们会跟我说,或许不会说,但我都要尽量让他们满意。”

聊天的时候,一个姑娘来修眼镜。她这也是找了别的地方,人家说修不好,才来到这里。
讲两件小事儿吧。
有个岁数大的先生上门,拿着个老款的旧眼镜来到店里。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有些东西不值得修理,而且修理比较麻烦,可能比买个新款实用品还要贵,于是刘宝祥首先告诉顾客,您修理的费用,可能足够买新的,甚至还要高几倍呢。
顾客一笑,“我来对了。”
并不是因为觉得刘宝祥诚实,而是顾客从前面的话里听出来,这个眼睛,刘宝祥能修。能修就行。
这是因为眼镜得来不易。这位顾客是“共和国同龄人”,她的妈妈答应,如果他考上高中,便会用一个月工资,给他买一幅眼镜。
“我一定要买一幅好看的。”
一个月工资是23块。这位先生真就考上了高中,接着,“把家乡所有的眼镜店都转了一遍,居然没有看得上的。既要找好看的,也要用尽这23块钱。”
最终,他找到了一幅据说是与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主人公一模一样的镜架。可惜这个顾客没有说到电影名字。
刘宝祥叹口气,“你说,这还是一幅眼睛吗?算起来,他考上高中到现在,已经快四五十年了。他的母亲也早已去世。”
修眼镜挺顺利就完成了,但是两个大老爷们,在店里聊了一下午天儿。说起过去的生活,自己的母亲,聊得那位先生眼泪汪汪。
“我要是修不好这眼镜,我都对不起人家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刘宝祥说。

工作中的刘宝祥。
另一件事儿是一个老太太,也是拿着旧眼镜来修,也是坚持要求修理。
修好了。50块钱修理费。结果当天晚上,刘宝祥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太太的女儿打来的。
“劈头盖脸就骂我,说我坑人,修个眼镜就敢要老太太50块钱。”
刘宝祥跟对方解释,这不是乱收钱,而且之前也跟老太太说了,这东西不一定值得修理,但老太太坚持要修的嘛。
刘宝祥这边儿觉得价格对得起工作,本来这事儿,人家要是觉得不值,抱怨抱怨也就完了。
第二天,老太太又来了。
一进店,先给刘宝祥道歉,“我的孩子不懂事儿。”再一聊得知,那个眼镜是老太太过世的老伴儿的物品。
前一天晚上,闺女给刘宝祥打过电话后,老太太和闺女聊了一晚上。她们一定是回忆过去的生活,虽然不知她们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但据老太太说,两人一起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闺女委托母亲,一定找到刘宝祥,给刘宝祥道歉。老太太照办。
“眼镜有价,但情感是无价的。”

刘宝祥的维修桌。
还有的顾客,拿着一副进口老眼镜来修理。“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半是修眼镜,半是显摆。“可是,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也难怪他想显摆。有这个眼镜,证明他的祖上是个读书人,文化人。”
连这种时候,刘宝祥都在站在顾客的角度上考虑。
“事儿做好了,钱自然就来了。”所以,只要把精力放在做事儿上,并不需要纠结于收入。

认真,是他认为最宝贵的经验。
他活的状态太理想了。令人羡慕。
经过口口相传,他的顾客如今遍布全世界。身旁摆着一摞快递,妻子帮他整理、发出,都是修理过的眼镜。甚至有些人因为信任他,连买眼镜配眼镜,也都找他办理。
“什么大使馆的,明星的,还有从欧洲寄来的。”这样的工作,让刘宝祥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啊。”
别小看这句话。经历过下岗风潮的那一代人,在职业方面的自信心,早已被体制磨平。难得有这么个刘宝祥,发出这样的感叹。
“现在想,当年我有点儿技术,这是抱着个金饭碗,却连自己都不知道。好在我的师父提点了我。”
话说回来,若是刘宝祥不懂技术,师父再好又能如何?

刘宝祥的小店。
除了感谢师父,刘宝祥说,从小的“手碎”,让他成为一个认真对待技术的人,“得益于认真二字。”
说到认真,他又说到了日本。不久前他去旅游,买了不少东西。“在店里,售货员一件件给包好,问你要什么颜色的纸,上面贴什么样的花。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她每天要面对多少我这样的客人?如果是在国内,哪怕换我做这个售货员,恐怕早就没耐心了。”
而发达社会“随处可见”的“认真”,让他感受到了另一种鼓舞。
或者,说句我们这个“不太认真”的社会常说的话,“深深的教育了刘宝祥”。

刘宝祥拿着一幅修好的眼镜,仔细检查着。
谢谢观看。今天本号下一栏,有为您简单整理的北京眼镜行业的发展历程。

来源:微信公众号 猫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