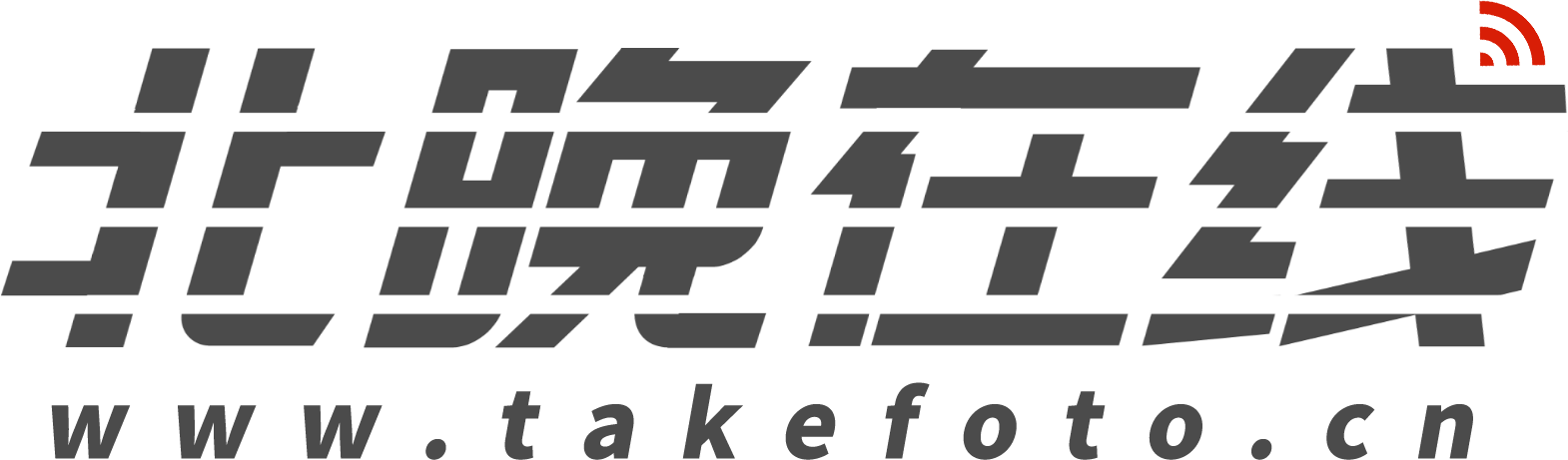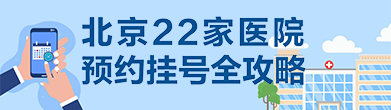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

公园偷偷埋骨灰?宠物墓地超万元?宠物“安葬生意”亟待规范
近年来,不少机构推出包括遗体清洁、告别仪式、火化安葬等项目在内的宠物殡葬服务。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家宠物殡葬店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宠物骨灰的处理方式也存在较大...
北京日报客户端 -

3C标志换个“马甲”接着卖,网络平台如何管?
6月26日民航局“充电宝新规”一出,“3C”立即成为热门话题。北京日报客户端接到多位消费者反映,网络平台上竟有不少商家售卖“3C贴纸”“3C印章”。记...
北京日报客户端 -

锐评|中国人的团结再一次具象化了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遭遇特大洪水,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眼下洪水逐渐退去,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天灾无情人有情。面对暴雨急流...
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