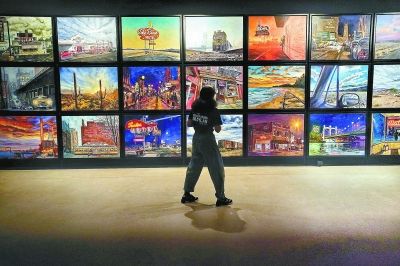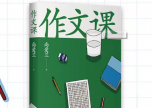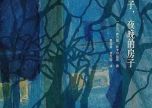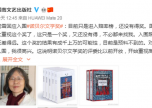上周末,推迟了时间、让人翘首以盼的诺贝尔文学奖爆了大冷门,宣布要把这顶桂冠戴在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头上。跨界跨得实在太大,若不是因了互联网能看实况直播,不明真相的人们乍一听定会将其作为一条洋葱新闻。
作者 张玉瑶

其实从1996年起,迪伦就被提名这一奖项,但可惜除了粉丝之外的人们从没太当回事:一来是之前名次太靠后,而来更主要的是心理作用作祟——人们想到了村上春树多年“陪跑”的命运,却不会想到瑞典的老先生们竟真的大胆到把一个文学奖颁给音乐家。
两边倒的争议从一开始就在发酵,支持者流下感动的泪水,大赞其“实至名归”,反对者则大摇其头,指斥诺奖此举是“侮辱了文学”。有意思的是,这一回人们并未单纯按照大众/精英、民间/学院的身份来站队,而是每一边的队伍中都有不同身份的拥趸。
迪伦的歌词在多大意义上具备文学性?其中体现的政治性是伟大的抗争还是对六十年代的跟风?其音乐带给人的是超时代的灵魂震颤还是怀旧者的一厢情愿?人们吵嚷不休之际,75岁的迪伦正在开巡回演唱会,面对这个新闻他一言不发,只是朝台下唱了一首歌:Why You Try to Change Me Now(为什么你们现在要尝试改变我)。据说到现在诺奖委员会还没联系上他,不知道他是否会去领奖。
然而我们并不能改变他。他还是这么酷。鲍勃·迪伦,响亮的名字。五十多年了,人们一直在挖掘他的一切,甚至有了一门叫做“迪伦学”的东西,但他如此善于用艺术来掩藏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我们对他始终一无所知。我们唯一确知的是,他一直很酷,挟着六十年代的革命风潮和“垮掉派”的气质,成为二十世纪闪闪发亮的文化象征。
鲍勃·迪伦向来拒斥媒体。演员、编剧斯科特·科恩在1985年有幸采访了他,之后这样写道:
鲍勃·迪伦,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离“弄明白”迪伦最近的地方,可能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惟一自传《编年史》(2006年国内首出中文版时名为《像一块滚石》,即他的代表歌曲之名,2015年再版改回原名)。这是迪伦不多的能够在传统书写意义上被作为“文学”阅读的文本。这本书他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仅仅写成了第一卷,但随即就在《纽约时报》的非虚构类排行榜盘踞了长达十九周,并获普利策奖——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就在跨界表演上收获荣誉了。
初读《编年史》这本书,对美国现代音乐史陌生的人多少会一头雾水:里面有太多的人名(很多都在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和专业音乐术语。更要命的是,迪伦没有按照惯常的名人自传路子来纪事本末、剖白人生,而是——借用他1963年那张专辑的名字,freewheeling,是“放任自流的”,或“随心所欲的”,或“自由自在的”。尽管书名叫做“编年史”,但却和编年的体例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一副标记了各种时间和事件的扑克牌,拿到哪张,就从哪里讲起。我们翻开第一章第一页,看到第一句话是:
路·莱维,利兹音乐出版公司的头儿,带我乘出租车去西七十街的皮提亚庙,给我看那个袖珍录音室。
仿佛平淡而突然的一句。然而迪伦是有他的叙事策略的:直到写书的2004年,他都把这个片段视作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和高光之一。坐上那辆出租车前不久,他刚刚被老牌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而后者即将为他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1962年)。在此之前,他只是个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酒吧、咖啡馆里表演的无名小子,能被著名的“煤气灯”酒馆接纳为固定歌手并为著名民谣歌手戴夫·范·容克伴奏,就能让他兴奋不已。
包括戴夫·范·容克在内,迪伦记下了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格林尼治村歌手的种种往事,为后来的人们重新回顾六十年代初由此兴起的民谣复兴运动提供了另一个样本。事实上,这个不满二十岁的无名小子在寒冬的暴风雪中坐着一辆四门轿车,从中西部北方的明尼苏达州一路驰骋来到纽约,正是为了来寻找这些“在唱片上听过的歌手们”——特别是他视为导师的民谣艺术家伍迪·格斯里。
在此之前,迪伦是个地道的小城青年。“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弹奏吉他。”他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迷途的家》中如是说道。1941年5月24日,他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6岁时举家搬到矿业城市希宾,那里轰隆的矿车后来成为他一些作品的灵感来源。很多年里,他靠着收音机来追随美国音乐动向。后来他到本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上大学,在那里接触了伍迪·格斯里们的唱片。于是他决定退学去纽约这个“世界的首都”,接触那些人的世界。“纽约市,这座将要改变我命运的城市。”“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从最底层的地方开始。但现在是命运显现出来的时候了,我觉得它正看着我,而不是别人。”
他大学期间还改了名字。“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而“迪伦”却是来自诗人迪伦·托马斯。他读了诗人的一些诗,并觉得“迪伦”听起来比“艾伦”响亮。这在暗中也标示了他日后同诗歌的关系。

“抗议”还是“反叛”?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被称作好汉?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道海
才能在沙滩上安眠?
炮弹要飞多少次?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这是迪伦最出名的作品《答案在风中飘荡》。1963年8月27日,马丁·路德·金在做了那个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后,迪伦用口琴和吉他唱响了这首歌。从文词上看,它在迪伦的众多词作里并不算得多么高超,但缘于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反战情绪,它和后来的“抗议专辑”《时代变了》强有力地代表了六十年代的声音——而也被视作了“抗议诗人”和民谣弥赛亚。
六十年代是个很不安宁的时代,冷战、种族、民权、独立运动、共产主义、越战、导弹危机……种种都动荡着美国人的信心。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发言人、一个旗手,而用奇特嗓音敲打人们神经的看起来无疑是最像的那个。
格林尼治时期的迪伦显得雄心勃勃。那时他有一个来自左翼家庭的女友苏西·罗托洛,也就是《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这张专辑封面上挽着迪伦走在冬日格林尼治街道上的女孩。她是他的缪斯兼导师,把他带入艺术世界,也带入政治领域,影响了他的歌曲创作。
不过更重要的是,是迪伦正在对他自己的音乐形式进行着探索。他发现了“民谣”,并确立其与现实直接的关联:“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或者接近它一半的事物了。”“我的曲目里没有一首歌是给商业电台的。堕落的走私酒商,淹死亲生孩子的母亲,只开了五英里的凯迪拉克,洪水,工会大厅的水灾,河底的黑暗和尸体。我歌里的这些题材可不适合电台。我唱的民谣决不轻松。它们并不友好或者成熟得甜美。它们可不会温柔地靠岸。”他大量地阅读以汲取灵感(按《编年史》里的列举,从福克纳到弗洛伊德,从普希金到克劳塞维茨,他的阅读量相当不小),甚至跑到纽约公共图书馆从微缩胶卷上阅读一个世纪前的报纸,了解南北战争前后的新闻。那些过去的事情往往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上唤醒他对于当下的意识。
但,时代的冀望和个人的意愿在多数时候并非完全契合。“旧的秩序正在消逝,/今日的风流人物将成为/明日的无名之辈,/因为这时代在变化!”尽管这些铿锵激越的作品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抗议歌曲”,迪伦却更倾向于将其看作“反叛歌曲”。从字眼儿上看,前者是政治范畴内的,而后者的内涵更加广泛,体现出一种尖锐的异质性,是“鲜活的,好的,浪漫的,和值得尊敬的”。
迪伦并不是非要以挺身抗暴的姿态出现,他只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美国在改变”,这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时代,是金斯堡《嚎叫》的时代,是打破主流的时代,是诞生新型街头意识和人格的时代。要有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了。他的词作中读得出兰波、惠特曼和“垮掉派”的气质,甚至“垮掉派”鼻祖、诗人金斯堡也承认自己在听到《暴雨将至》这首歌时嚎啕大哭。
美国桂冠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曾邀请为自己的戏剧写歌,并告诉迪伦说,他是个“严肃的诗人”“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他的作品“将被以后的几代人当成试金石”。出自诗人之口的评价肯定了迪伦的时代价值,当然也加持了其文学性。最终是诗/歌本身,而不是其他,能够超越时代。

拒当“代言人”
对于迪伦来说,“反叛”的内涵比“抗议”大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他很快就结束了“抗议”的阶段,却一直在“反叛”。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已经声名赫赫的迪伦出人意料地抱着一把电吉他上了舞台,结果激怒了观众,被嘘了下去。对看惯木吉他的人来说,他的这一举动显然是“背叛”了民谣。但从那一刻起,他开启了一个民谣摇滚的大门。
更令当时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想要彻底放弃使自己声名鹊起的“抗议歌手”的身份。他做出这个决定如此之早——早在人们的热切期望之前,早在风起云涌的1968年之前,音乐风格就变了。外界认为这和他遭遇了一场摩托车车祸有关,而他自己在《编年史》中说也是和新组建的家庭有关。1965年,他和萨拉结婚,生儿育女,“在家庭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保持真正的兴趣”。书中有这样一大段吓人一跳的话:
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想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我替整整一大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我确实从来都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写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根据迪伦自己的描述,他们一家那些年的生活相当狼狈。“全国各地肯定都有指向我家的路标”,他们四处搬家,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却总逃不掉追随而来的人。记者们从未放松追踪,朝圣者们破门而入,还有无数的游行示威者要求他像群众领袖一样站出来指路,不再逃避作为“一代人的良心”所应肩负的责任。
“我对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有何亏欠?没有。一点也没有。”从嬉皮时代经历过来的他继续用有些嬉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麻烦,设置迷雾,敷衍公众眼睛,让自己构成了新的难以猜透的形象。他甚至还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录制了一张专辑,任评论家们过度解读。
远离“符号”,如脱钩之鱼,“名声本身就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可以剥离的东西”。迪伦看得很准。果然,又是很快,世界平静下来了,轰轰烈烈令人难忘的六十年代落幕了。
在路上
《编年史》出版后,人们很快指出其中有着诸多虚构和杜撰,迪伦使他自己成了谜。作为迪伦众多传记作者之一的戴维·道尔顿说,这因为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他“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神话躯壳——并且将其覆于自身之上”。他写的是“鲍勃·迪伦”的历史,而不是“罗伯特·齐默曼”的历史。产生意义的是前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不仅用迪伦的歌名“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作为他研究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著作的名字,还把他在1974年看的一次迪伦演出视作六十年代之投射的结束时刻。“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彬彬有礼的人怀着同代人团结一心的激情向前涌去”。
这个属于特定一代的场景令人唏嘘并感动。然而那些期待“forever young”(永远年轻)的人未必想到,八十年代,即便迪伦自己也曾陷入“过时”、“被文化遗忘”的忧惧,觉得自己注定停留在六十年代的符号里、像“一艘烧毁过后的空空的破船”,也依然没有停止创作和灵感乍现。他步入中老年后,开始对巡回演出产生兴趣,三十多年里走过世界许多地方,一场接一场,75岁高龄仍不停休。或许,他是想把歌引回源头吧——那样看起来好像更接近吟游诗人。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