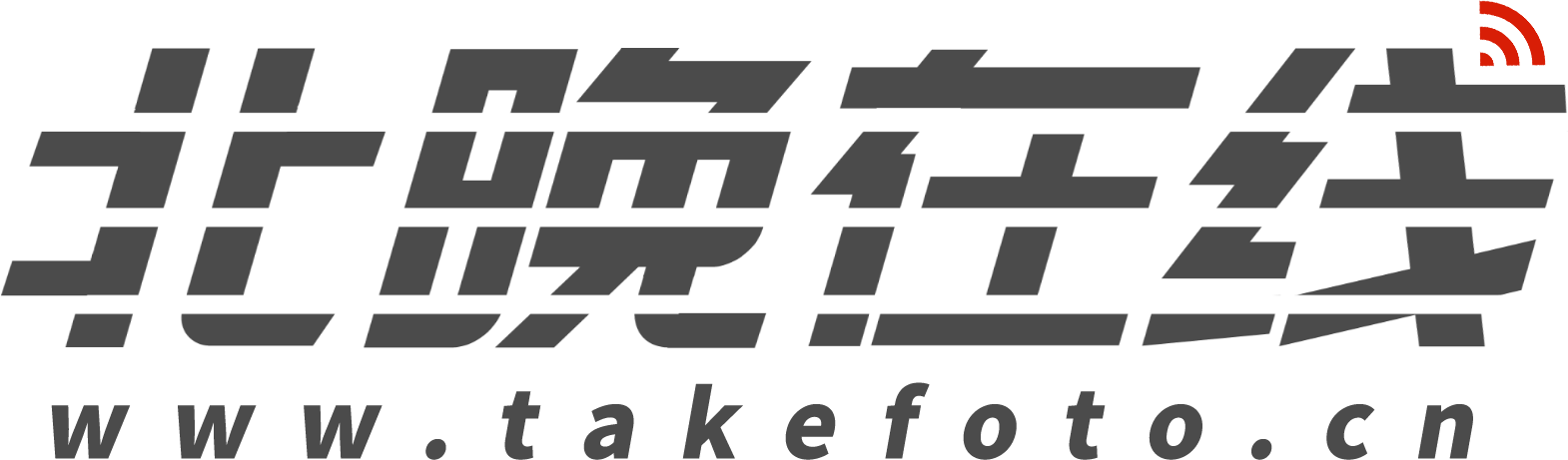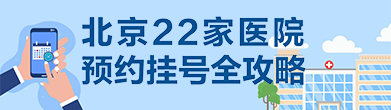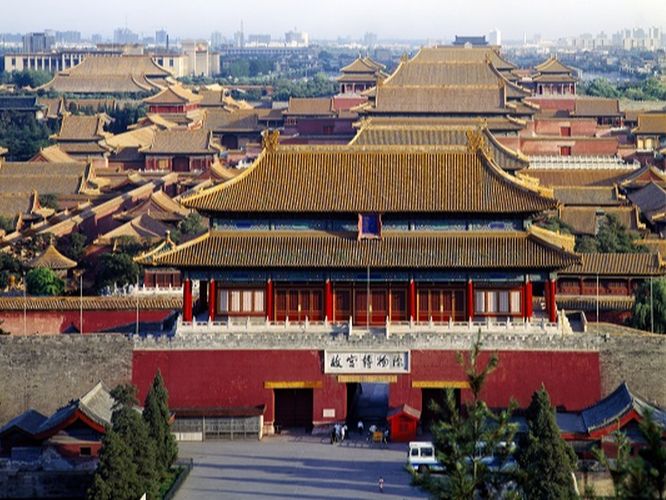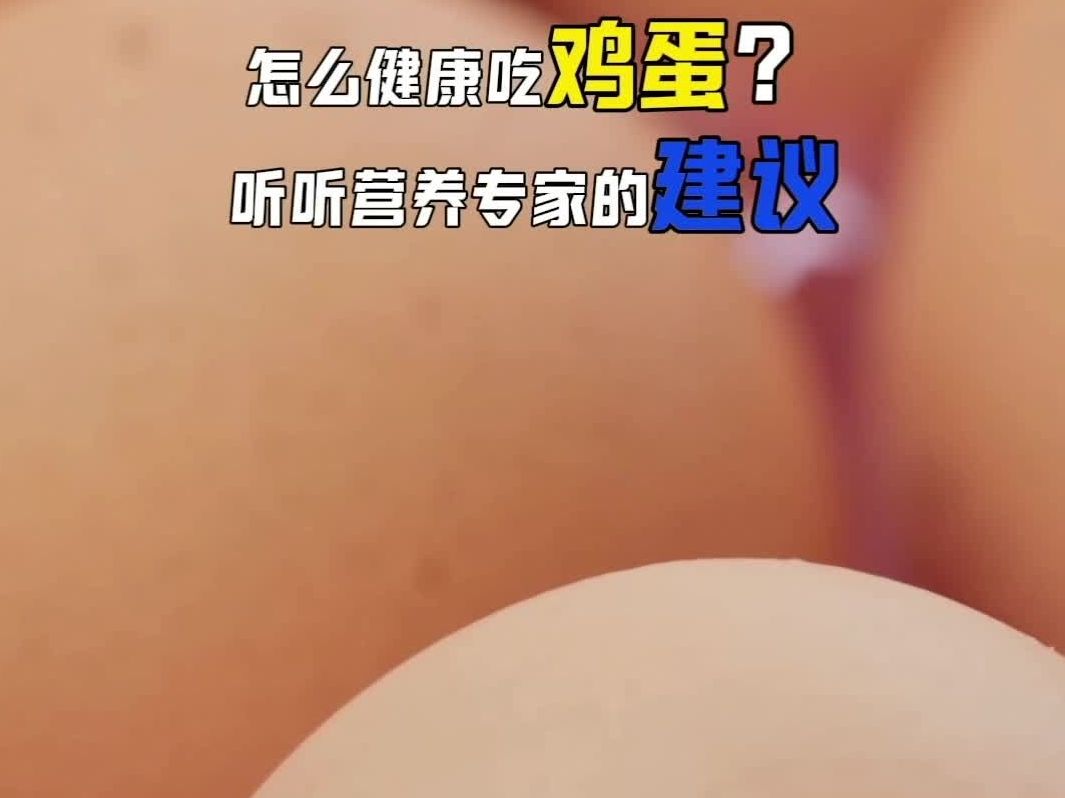-

说说“容易”与“不易”
前不久出门上街,路过银行时,想取一点钱。一摸兜,既没带银行卡,也没拿身份证,心里嘀咕:这事儿恐怕不容易办。谁知走进银行一问,工作人员微微一笑:“可以取,到前台扫码就行。”...
人民日报 -

人民锐评:越是AI,越需人文
今年的全国两会,“人工智能”成为高频词。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迭代,深入影响社会各行各业,也日益走近人们的日常,甚至在某种程度...
人民日报客户端 -

“中国购”正成为认识中国的新方式
从精美的国潮文创到优质的智能家电,从便捷的移动支付到高效的离境退税,丰富的商品、多元的购物体验让外国游客认识中国有了更多更鲜活的载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入境消费环...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