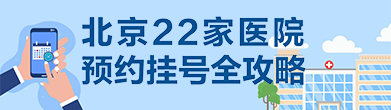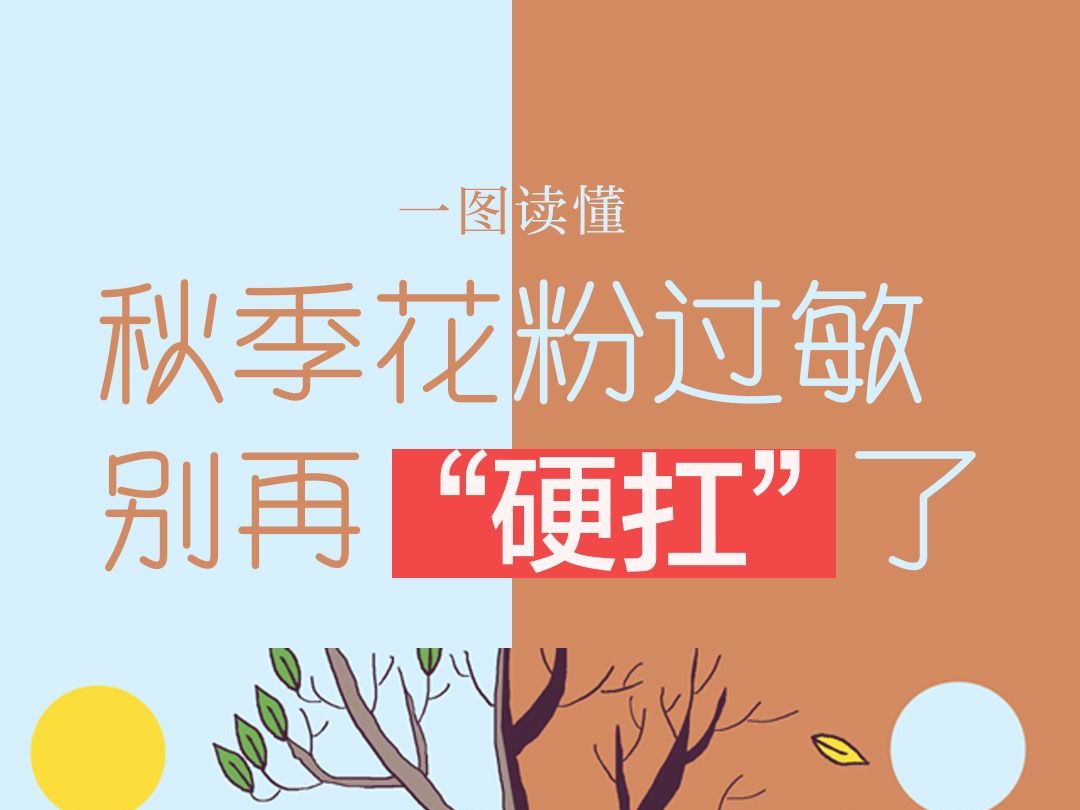-

父亲遗留餐馆五个子女谁继承?多部门联动助经营权顺利变更
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家经营多年的餐馆,餐馆的经营权该如何传承?成了5个子女的心病。北京西城区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市场监管所三方联动,顺利完成经营者变更,最终子承父业,店铺传...
北京日报客户端 -

AI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未成年人成家庭数字技术“导师”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正在家庭、学校与平台之间形成联动共生的新格局。9月24日,《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5)》发布,对我国未成年...
北京日报客户端 -

地铁站名“名不副实”误导乘客,乘客跑了冤枉路
临近双节长假,北京的天气也逐渐开始秋高气爽,又迎来旅游高峰。有些市民或外地来京游客在出游时发现,北京部分地铁站“名不副实”,因此跑了冤枉路。 北京地铁已有车站超500座,...
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