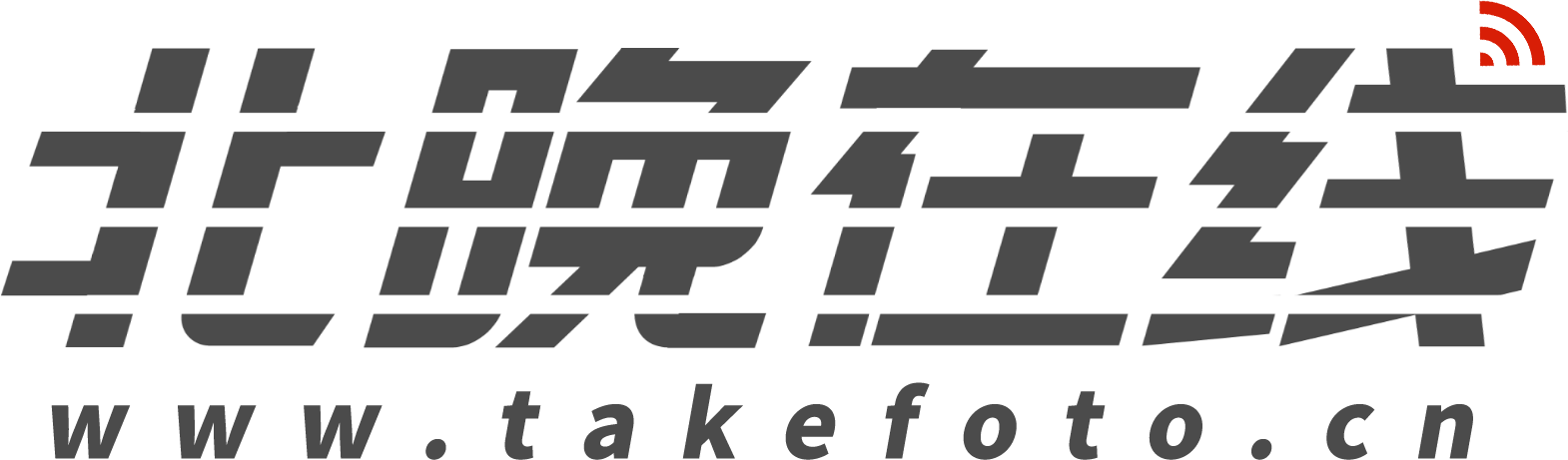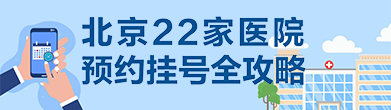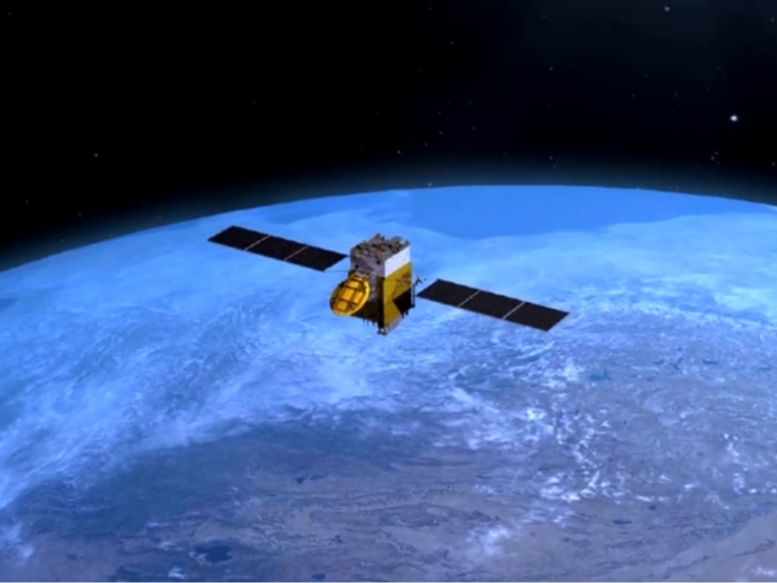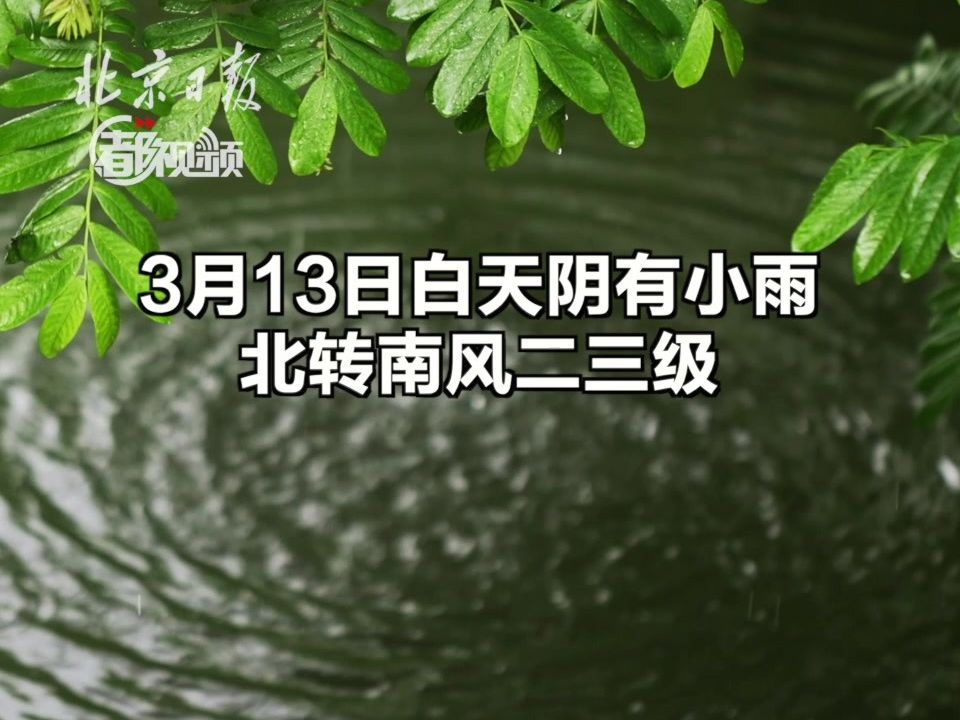-
锐评 | 中国再次给了世界值得信赖的确定性
全国两会胜利闭幕。 大会期间,全球媒体扎堆北京,报道数量继续大幅增长。“赢得未来的计划”“让合作伙伴感到踏实”“世界动荡之际,中国引领未来”…&helli...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中国购”正成为认识中国的新方式
从精美的国潮文创到优质的智能家电,从便捷的移动支付到高效的离境退税,丰富的商品、多元的购物体验让外国游客认识中国有了更多更鲜活的载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入境消费环...
人民日报海外版 -

遇题只会“拍照搜”?AI正在废掉这一代孩子的思考能力吗?
“不少作业和论文的AI痕迹过于明显,这样下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可能会被削弱。”在高校教授文学概论的王老师的担忧,正成为越来越多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共识。AI在带来效率与便利...
新华社